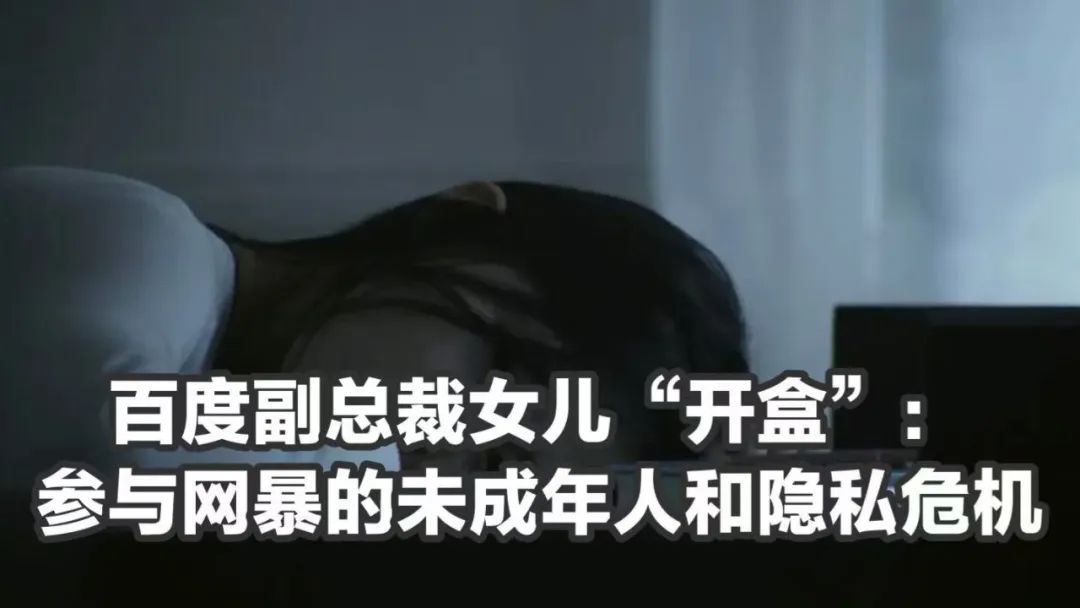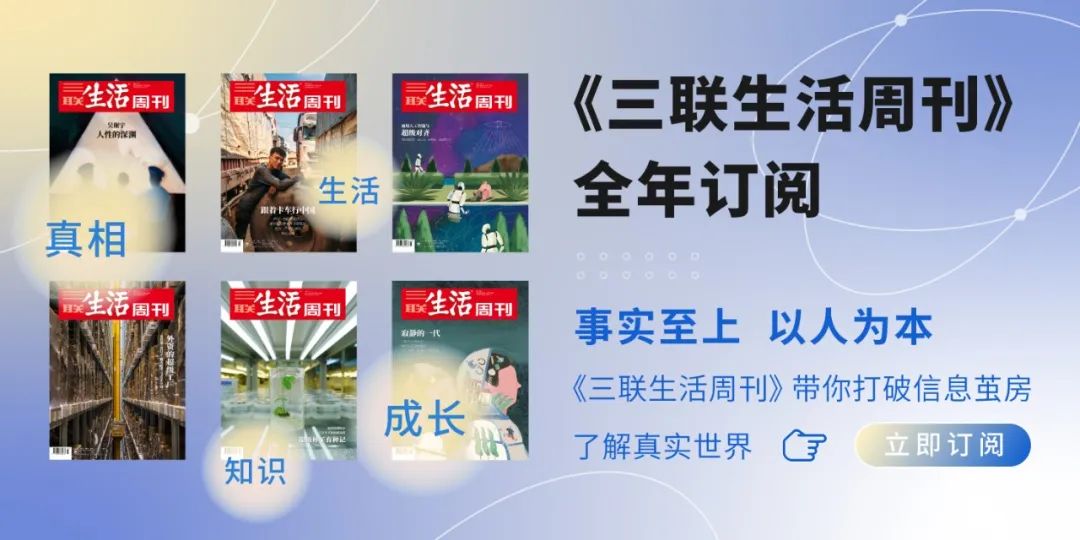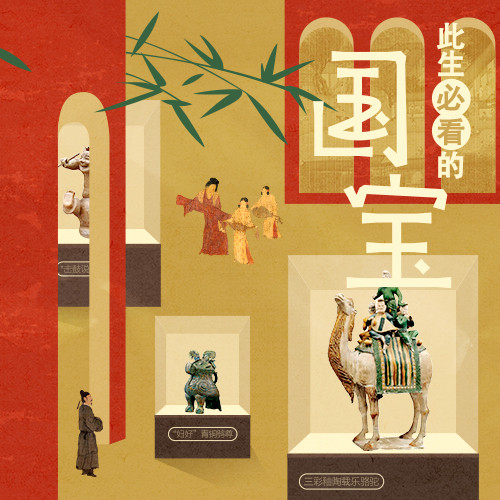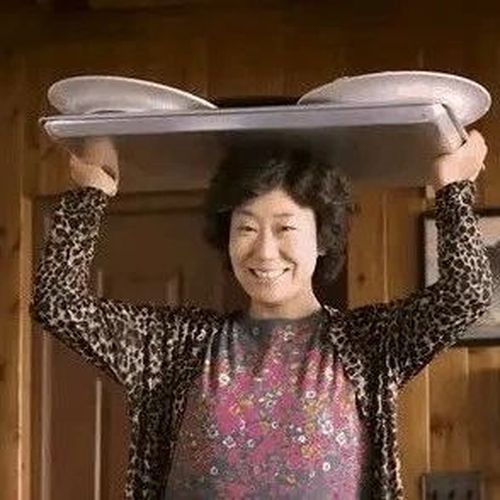花7700元,我办了一场“嫁”给自己的婚礼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4-02·阅读时长29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一个人的婚礼:自我重启
社交媒体上,小然穿着一条哥特感的黑色婚纱裙在香格里拉举行了一场“一个人的婚礼”,婚礼的来宾是在“结婚”当天,通过手绘邀请函请来的60多名陌生人。这条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6.6万的点赞量。视频下的大部分评论都充满了善意和支持,他们认为,和自己结婚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是一种爱自己的表达,也有人对此无法理解,并将其与“孤独的最高等级”画上等号,抑或是博人眼球的社交流量密码。

在香格里拉,小然的“一个人的婚礼”(受访者 供图)
在社交媒体上宣称与自己结婚的女孩不在少数。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几位女性聚集在西班牙的北部城市毕尔巴鄂(Bilbao),公开表达对自己的爱意,并举行了和自己的结婚典礼。“自婚”,指的是一种以加强自我关爱为目的而与自己结婚的行为,旨在打破社会长期以来对单身生活的消极偏见。
我最好奇的是,那些选择自婚的女孩怎么看待“自我”在爱情中的位置,自婚行为给她们的人生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和自己结婚,完全是一场临时起意。从决定到结婚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此前,小然在丽江的乡村小学里支教,她教孩子们唱歌、朗诵、画画。香格里拉之行算是这次云南支教的终点。小然说,这场和自己的婚礼,就像是送给自己的成人礼。小然30岁的时候,发生了太多失败的事情:创业八年的品牌没有熬过这个经济寒冬,与恋爱四年的男友分手,起因是对方对于进入婚姻表示迟疑。小然的经历让我想起英国作家索菲·坦纳(Sophie Turner)写的小说《我和自己结婚了》中女主人公克洛伊的经历,人生赛场过半,35岁的克洛伊刚刚分手,升职失败,一切好像都不对劲。克洛伊在流过了无数次眼泪,喝了很多次酒之后,决定和自己结婚,并且要办一场盛大的婚礼。索菲·坦纳写道,“我愿意做自己亲密的爱人、忠诚的战友”。我和小然提起这本书,她觉得克洛伊很像自己。
小然自婚的筹备过程和一场真正的婚礼并无二致。场地布置、服装化妆、邀请函与签到板、婚礼宾客……小然联系了一家当地的婚庆公司筹备场地搭建。一开始,婚庆公司以为是一场正式的婚礼,还提出了非常复杂的方案。小然不愧是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创业的姑娘,虽说对婚礼没有太多经验,但她自己画了场地搭建图,简化了整个方案,并极有效率地让其落地实施。咖啡馆老板被小然“自婚的故事”打动,免费向她提供场地。婚礼上摆放食物的长条桌布是小然向民宿老板借的床单。没有精美的印花邀请函?小然手写邀请函,充满诚意。没有宾客?她向陌生人发出邀请,随缘的心态中充满惊喜。这是小然在前半生最疯狂的一次体验,也最接近她期待拥有的生活——自由、洒脱。在黑色和白色的婚纱礼服之间,小然选择了黑色。“从今往后,我不想再做循规蹈矩的人,一切都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婚礼筹划比想象中顺利,租婚纱200元、场地台子搭建1000元、化妆500元,招待宾客的食物占了整个开销的大头,6000元。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一场婚礼就准备好了。
下午6点,婚礼倒计时前10分钟,小然正抱着婚纱的裙摆蹲在咖啡馆窄小的后厨里,她等待着婚礼开始,竟然紧张起来。在小然心里,这场婚礼是神圣且郑重的,它既不是玩闹,也不是为了流量。小然脑海里闪现出在经历事业和失恋的双重打击下状态极差的生活,两个月的时间里,她闭门不出,通宵失眠、酗酒,白天睡觉,又在夕阳西落时醒来,看着天快黑了,整个人心情越发绝望。小然的求助方式是找朋友们聊天,朋友们也都会劝她,30岁就是要吃尽爱情的苦。小然是从出生到30岁都一路顺遂的姑娘,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生活主动权总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但30岁时,生活的无力感就这样袭击了她。两个月里,原本体重不到100斤的小然掉了14斤的体重,瘦脱相了。

在香格里拉,小然的“一个人的婚礼”(受访者 供图)
她坦诚地告诉我,其实,这场婚礼的现场,她的现任男友也在,甚至帮她一起绘制并分发了邀请卡。现任男友是小然多年的普通朋友,是属于曾躺在联系人里的那一种。他带着很多年的好感,再次出现在小然分手的低谷期,在倾听与抚慰的过程里,小然感受到了两人三观的契合而渐渐从朋友变成恋人。采访前,我以为小然的婚礼是单身主义宣言的仪式,现在看来,她的自婚更像是历经生活重创之后的“自我重启”。
小然站在一个人的婚礼上,没有司仪问她,她自己问自己。“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你愿意好好地爱自己吗?我愿意。”小然的声音不自觉地有些哽咽,台下的很多陌生女孩在偷偷擦拭眼角。那场婚礼上,很多女孩哭了,她们或许想起了很多自己的伤心往事,她们彼此拥抱、互相安慰。小然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哭花了妆的女孩,她羡慕小然的勇敢,迟疑了许久,她告诉小然,她喜欢的是女孩,但却没法鼓起勇气迈出一步。
我问小然,现任男友怎么看待你一个人的婚礼呢?
在婚礼上,她用目光四处搜寻着男友的身影,但无论如何都找不到。等婚礼结束之后,男友告诉她,“我在一个很远的地方看着你,这个婚礼,我觉得应该完完全全属于你自己”。
街头新娘:“爱自己”宣言
作家索菲·坦纳在写《我和自己结婚了》这本书之前,曾在2015年走上街头,宣布与自己结婚。当年她的行为成为风靡英国网络的事件。接受采访时,她说:“自婚就是发表声明并创造一种文化观念的转变。我想证明热爱自我和爱上他人一样重要,但是由于没有现成的仪式,我想我可以借鉴婚礼形式。”索菲·坦纳走上街头,把手中的向日葵抛向蓝天。大多数人表达了美好的祝福,但在社交媒体上,她和小说里的女主人公一样经历了一番来自媒体的讨伐,“嫁给自己的举动似乎的确激怒了其他人——我被批评为自恋狂和博眼球,我被称为怪物、疯子,一个需要被社会监管的疯子等等。”

八年之后,同样还是在英国伦敦的街头,中国女孩李要红(艺名)穿着婚纱走上街头,她大声地告诉身边的人,“今天我和自己结婚啦!”在社交媒体上,这条洋溢着快乐生命力的自婚视频被她置顶,点赞量高达6.4万。镜头里,李要红穿着很像维维安·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风格的朋克蕾丝婚纱,配上一双帅气的黑色长靴走上街头。一路上,快乐自由的中国女孩吸引了不少路人,他们和她拥抱,合影留念,牵着她的手跳舞。最让她感动的是,一个姐姐得知她和自己结婚,直接从手上摘下一枚戒指送给她,并告诉她,“你结婚怎么能没有戒指呢?”李要红说:“和自己结婚的那天太快乐了!”世界展现出极为友善的一面,这场街头婚礼收获了所有人的祝福。相较小然的“一个人的婚礼”,李要红的街头婚礼让我想起《重塑爱情》中的一句话:“爱自己是一件朋克的事情,一件革命性的事情,一件激进的事情。”用在她的身上十分贴合,自婚是一则“爱自己”的独立宣言。
成为“街头新娘”,更像李要红关于“爱自己”的行为艺术。李要红的家境一般,所以她在英国留学的费用除了朋友资助的几万块之外,其余的都是自己贷款。留学期间,她不得不一边上学一边工作还债。去年,李要红研究生毕业,偿还完了所有的债务,并且结束了一段纠葛的情感。“我对我自己说,我终于可以好好爱自己,我可以启航去探索新的世界了。”李要红向我解释这场街头婚礼的意义。
1996年出生的李要红有一个父母离异的原生家庭,所以她对于婚姻其实没有特别的向往,“任何关系的尽头都是分别”是她的悲观底色,选择留学也是想要离家远一些。“靠自己”这三个字印刻在了她的心里。靠自己留学,和自己相处,陪伴自己,自己永远是自己最大的支持者。“我跟自己结婚,就是想不断地增加自己的价值。你如果想要去维持一段关系,就需要你能够给他人提供源源不断的价值。”

李要红在伦敦街头的“自婚”,让她收到了很多善意的祝福(受访者 供图)
提高自我价值的办法,李要红说只能靠“学习”,她原来还称自己为“学习博主”。上学那会儿,李要红是个举手回答问题都会脸红的女孩,她会刻意训练自己的短板,把自己培养成一名“社牛”。害怕在大众面前发言,她就跑到公交车上去给陌生人演讲;想做互动脱口秀演员,她从零开始了解段子怎么写,然后慢慢通过去脱口秀俱乐部做主持人锻炼即兴能力。“在见过很多观众之后,你就知道你和不同的人怎么聊天,怎么样去开玩笑,他们依然会觉得不受冒犯。”在李要红的世界里,一切难题都可以通过有效的方法解决。
在国外,年轻人之间流行dating文化,恋爱的基础是三观、习惯与爱好。李要红说:“多和不同的男生约会,通过相处,了解彼此的需求是否一致很重要。”李要红在发布自婚视频后不久便迈入了一段全新的恋爱关系。男友身高1.88米,长相酷似“吸血鬼”,这个英国男孩有着四分之一的意大利血统,还是一名爵士音乐人。之后,李要红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含男友量”变高,很多的视频创作也与撒狗粮的爱情有关。
之前在社交媒体上,李要红有一个深受粉丝喜欢的系列视频《专门搭讪外国帅哥美女》。李要红总是大胆搭讪,全程开麦。认识男友是在英国时装周的after party上,从搭讪采访开始,李要红的土味情话让后来的男友颇感羞涩。没想到发布之后那个视频就爆了,你来我往,在确定恋爱关系之前,他陪着李要红回中国一起参加活动。也是这次回国,打开了两人爱情的大门。“当时他不小心喝了一口鸡尾酒,而他对酒精过敏,我给他买药喂水,抱着他跟他说一切都会好的。回国的飞机上,他做我的人形靠枕,没想到他竟然还偷拍下来。”李要红践行了那句话,“勇敢的人先享受生活”。
他们一起在伦敦看了极光,他陪她在海边微醺跳舞,她和他一起在双层彩虹下许愿,他们将电影《爱在日落黄昏时》具象化……听到这里,不要以为李要红是一个恋爱脑。“你认为是这段爱情治愈了你吗?”她回答:“不,是我治愈了我自己。因为忠于自己,我才能找到他。”他们既亲密又时刻保有独立的空间,这一点松弛与勇敢,正是男友爱上她的最重要的特质。
自我与亲密关系
“一个人的婚礼”给小然带来了怎样的变化?你很难获得确切的某种标准答案,但它的的确确给小然带来了对于亲密关系的反思。
小然在上一段爱情关系里有很多困惑,她说不上是爱情里具有讨好型人格的那一类,但倾向于在为对方付出的状态里收获快乐。在“付出认知”上,两人有着明显的差异,男生会认为,你对我的付出应该具体表现在“为我做一顿饭”,小然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做饭“小白”,对方的需求恰是她的短板,她更关注的是另外一些事情:比如在社交应酬里,她脑袋里排序第一位的是能不能给男朋友争取些机会。或许是男生的自尊作祟,他更希望这些事情自己解决。在那段情感关系里,“错位需求”时不时发作,小然陷入了自我怀疑,回家还请教妈妈,“妈妈,我是不是应该去学习做饭?”潜台词里,“会做饭”似乎与“婚姻”画上了等号。小然的妈妈虽然也会催婚,但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还是会告诉她,放低自己的爱情并不能长久。
小然聊起父母堪称楷模的“爱情范本”,“我妈和我爸结婚之后,爸爸对妈妈说,‘你不可以只做家庭主妇,这样我们两个会有很大的差距’。两人结婚后,我爸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妈送到对外经贸大学去念书。”可以说,小然的父母爱情是自我在婚姻里成长的楷模。

《幸福到万家》剧照
分手之后,小然不断地复盘,爱情关系里的对错很难讲,但一个要苹果,另一个给香蕉,注定了它的悲剧性收场。如果早些看清楚自己和别人的需求,便也知道早些放手才是正确的选择。小然是摩羯座,用她的话来说,她是一个计划感超强、一切都不能失控的人,不仅是爱情,事业也同样如此。然而,这场自婚,打开了她人生的下半局。“我是一个有些悲观的人,即使是一场属于自己的婚礼我都很害怕,比如在台上忘词儿了怎么办?邀请函发出去没人来参加会不会很尴尬?”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倒是陌生人的祝福给了她不少惊喜。和现在的男友在一起后,小然感受到自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她放弃了控制与计划,等待爱情自然生长,结成婚姻。“我现在觉得,最浪漫的求婚,或许是我们两个人躺在床上,他突然对我说,‘我们明天去领证吧!’”
与小然“完美爱情样本”的原生家庭相比,李要红的原生家庭是另一种模样,可谓开局不利。李要红在大学有一段风平浪静的“健康爱情”,在这段亲密关系里,她照见了很多自己的问题。比如很难有安全感,情绪容易被对方激发而失控。李要红说:“原生家庭对于婚恋和亲密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不是所有事情都要让原生家庭背锅。”李要红一直在努力学习的便是看清并解决自我的困境,出国留学的人生对于她而言就像是一次二次成长。
李要红说,出国留学的这些年对她的婚恋观影响很大。她说,在东亚社会,无论是亲密关系还是亲缘关系都有缺乏边界感的表现。亲密关系中,过去我会认为,如胶似漆的关系是好的,所以很多以“爱的名义”实施的控制在无意识中产生。我们常常会习惯将“让自己变得更好”这个事情寄托于一段美好的情感关系中,一旦关系破裂,自我也很容易碎裂。在国外,她很喜欢彼此既有独立空间,又有甜蜜的共享时刻,爱情与自由都不耽误。不仅如此,亲缘关系的边界感也让她刷新了对家庭的看法,她举例说,男友曾有八年的时间一边旅行一边在路上赚钱,后来因为自己还有一个音乐梦想才重新回到伦敦。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很少有开明的父母允许自己的孩子过这样的生活。
关于什么是理想中的爱情,李要红说:“我的浪漫是自由,而他给我的浪漫是陪我一起自由。”这与1992年的加拿大女诗人鲁皮·考尔(Rupi Kaur)写的诗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不要你填补我的空虚/我想一个人变得充实/能够照亮整个城市/然后我想要你在我的身体里/因为我们俩人一起/可以点燃火焰。”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5-6期,文中小然为化名)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大家都在看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5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5924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