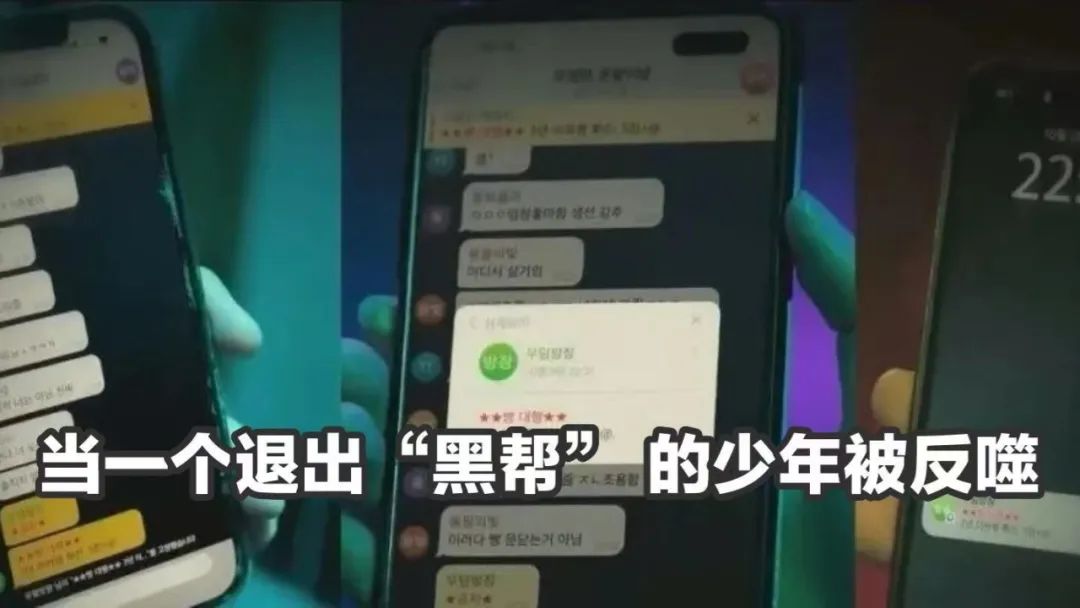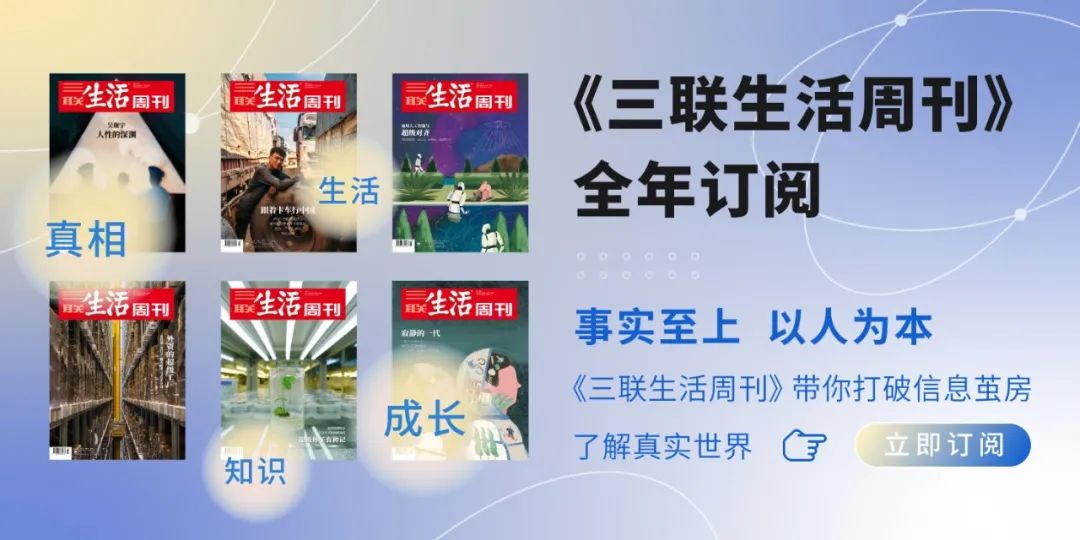“光鲜亮丽、情绪稳定的新手妈妈,只存在于网络”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今天·阅读时长31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我的每一位采访对象都是从这样一句话开始她们的讲述的:客观地说,我的条件已经很不错了……生产前,有收入不错的工作,经济独立;生产后直接住进条件不错的月子中心,尽可能多地得到休息;回家后长期雇用育儿嫂,预算充足;父母长辈能随叫随到地帮忙看孩子;房子够大,空间不拥挤……和很多人相比,面对育儿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这些妈妈可以说是有些底气的。然而,她们都对我说:按道理来讲,我不该有产后抑郁啊……
2023年《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显示,我国产后抑郁(PPD)患病率达14.7%。这并不是说,那些没有被诊断为产后抑郁的妈妈就过得顺心。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研究,50%~60%的产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产后情绪波动。
我和身边的妈妈们聊了聊,发现光鲜亮丽、情绪稳定的新手妈妈似乎只存在于网络上。大家似乎都有一肚子苦水要倒。一个备受期待的新生命的到来,为什么反而让人变得不开心?养育一个孩子为什么变得那么难?
记者|孙若茜
我的每一位采访对象都是从这样一句话开始她们的讲述的:客观地说,我的条件已经很不错了……生产前,有收入不错的工作,经济独立;生产后直接住进条件不错的月子中心,尽可能多地得到休息;回家后长期雇用育儿嫂,预算充足;父母长辈能随叫随到地帮忙看孩子;房子够大,空间不拥挤……和很多人相比,面对育儿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这些妈妈可以说是有些底气的。然而,她们都对我说:按道理来讲,我不该有产后抑郁啊……
2023年《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显示,我国产后抑郁(PPD)患病率达14.7%。这并不是说,那些没有被诊断为产后抑郁的妈妈就过得顺心。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研究,50%~60%的产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产后情绪波动。
我和身边的妈妈们聊了聊,发现光鲜亮丽、情绪稳定的新手妈妈似乎只存在于网络上。大家似乎都有一肚子苦水要倒。一个备受期待的新生命的到来,为什么反而让人变得不开心?养育一个孩子为什么变得那么难?
记者|孙若茜
妈妈成了工具
三个月大时,小花就开始拒绝吃奶了。三个月大的孩子,不肯吃奶等同于绝食。两年前,当多比告诉我这件事时,我以为她在开玩笑,至少有些夸大其词。当时,我的脑子里就蹦出一句话:饿他三天就什么都吃了!这是我的奶奶特别爱说的话。我想起奶奶笃定的语气,相信这办法久经考验。于是,我问多比:饿一饿呢?她说:没用。医生告诉她,如果小花连续48小时达不到一定摄入量,就会有脱水的危险。她不敢试探,不敢让小花靠近边界。
没人知道小花为什么不吃奶,医生猜测是心理原因,像这样的情况,一千个孩子里大概会有六七个,他们对此也几乎束手无策。极端情况下,医生会向孩子胃中插入导管引流,这是下下策。最好的办法只有“尽量想办法喂”。
多比用拔掉针头的注射器向小花的嘴里打奶。学生时代,她就是这样养活过一只路边捡到的巴掌大的小猫。可小花不是小猫,最关键的是要趁其不备,所以通常需要三个人配合,一人抱小花,一人拿绘本或玩具吸引小花的注意力,剩下一人负责喂奶。小花沉浸在其他的事情中,才会在不知不觉间把奶吞咽下去,否则就会全部吐出来。别的宝宝用10分钟就能喝完的奶量,小花至少要用一个小时。

从三个月大直到小花满周岁,喂奶都是小花一家每天的头等大事。在多比的记忆里,每一天,每隔一会儿,她都要用一声叹息启动自己,然后拿起注射器,一个10毫升,又一个10毫升,不敢懈怠……关于那几个月,她不记得自己如何逗小花笑,她们在一起做过什么游戏,她留下的所有记忆几乎都与刻度有关。直到现在,每当多比见到别人家的孩子抱着奶瓶发出咕咚咕咚的吞咽声,都忍不住停下脚步:“这样的幸福我们家一刻都没有享受过。”
到了小花能吃辅食的月龄,多比还在发愁。我问她:不能用米粉替代吗?她告诉我,医生给她出了一道换算题——已知每100克奶粉含有多少铁、多少钙、多少蛋白质……如果想要获取同等的营养,需要吃多少米粉?米粉中该加多少肉、多少菜?用不同品牌的米粉做这道题,结果一样吗?接着,她流利地说出一串串数字,一个个精打细算之后的结果,就像一个会计,令我震惊——大学时代,她差点会计学挂科。我想象她左手一罐奶粉,右手一罐米粉,目光在两个成分表中不断穿梭的样子,就好像一个天平。她纠正我:是痛苦的天平!
那段时间多比几乎每天都在哭,躲在房间里的时候哭,下楼遛狗的时候也哭,邻居看见了就劝她:孩子怎么都会长大的!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这话有道理,可当时只要小花有一顿奶没吃,她就觉得自己的日子过不到明天了。
小花这样的孩子固然是罕见的,但我能理解多比当时的焦虑。在我的孩子出生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当他睡得无比安静时,很多次,我都忍不住凑近去试探他的鼻息。孩子长大后,我把这当作笑话讲给我的朋友们听,结果竟发现几乎每一个新手妈妈都做过同样的事,每个人都曾经小心翼翼、过分担忧。还有个朋友告诉我,坐月子的时候她看到宝宝吐口水泡泡,又看到有人在小红书上说这可能是肺炎的表现,她很害怕,每时每刻盯着孩子的嘴。后来她干脆买了个听诊器,时不时就贴在孩子胸前。
孩子就像一张考卷,卷子展开之前,你永远不知道真正的考题。孩子从不按常理出牌,因此养育的过程经常会让人觉得:学的全不考,考的全不会。
心理咨询师宫学萍告诉我,很多人的产后抑郁来自养育过程中的挫败感。她提到,如今的新手父母大多是独生子女一代,绝大部分人的生活环境中没有婴儿鲜活的成长过程,婴儿只存在于杂志上、广告里、邻居家……即便孕期读再多的育儿书,搜集再多的资料,当婴儿真正到来,带来的依然是完全陌生的感受:脆弱、不可能沟通、无秩序、没道理可讲。

然而,这些新手父母在成长过程中,从学校到社会,所有被考核和被表彰的能力都是包含管控力、自制力、计划性的理性思维,与抚育婴儿时面临的考验大相径庭。挫败带来的不适,会使人本能地向外攻击或自我攻击,就制造出了冲突或产生了抑郁。
社会学者刘汶蓉在接受采访时首先提到的是“孤独育儿”的概念。过去,养育一个孩子可能会借用一整个村庄的力量。这种帮扶既包括分担照看孩子的实际任务,也包括提供一套比较完整的养育经验,它的存在通常能在很大程度上消解新手父母对未知的焦虑。当社会流动使家庭越发小型化、孤立化,亲属网络对育儿的帮扶也随着熟人社会消失而消失。如今,照看孩子的任务要在小家庭内部完成。在这个过程中,顺延社会的传统观念,新妈妈成为养育的“第一责任人”,承担的责任和压力自不待言。
与此同时,在“科学育儿理念”的传播之下,长辈的养育经验大多“失效”——过去的经验或者不再适用,或者不被信任。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新手父母往往每件事都要去比较、去求证,然后按照所谓的标准答案执行。
今天的妈妈,很容易从网络上获取海量的育儿信息。这些信息很多基于群体研究的结果:几个月大的孩子,应该有多高、有多重、吃多少毫升奶、睡几个小时觉,各项运动能力应在何时达成……这些均有据可查。另一些信息基于个体的经验:我的孩子长得快,因为我做到了……
信息即标准。然而,孩子并不是标准零件。偏差总会发生,一旦被视作“不达标”,母亲的焦虑就随之而来。

一个朋友说,她的孩子出生时五斤多,个子有点儿小,家里人生怕孩子发育有问题,就把婴儿的体重秤摆在客厅中央。每天晨起、饭后、临睡,孩子都要被放上去,定点测量。
刘汶蓉说,当育儿者与孩子相处的每一步都需要去搜索、求证、被指导,就意味着他/她在这个过程中完全失去了自主性,被“对还是不对”的焦虑所控制,就会失去自信。比如,孩子哭了该抱还是不抱?该饿了就喂奶还是到点才喂?当这些原本应该建立在母亲对孩子独特生命状态的体察之上做出的决策,交给了统一规范的科学理念时,母亲就几乎被异化为养育的工具,难以从养育的过程中获得幸福和享受的体验。
母亲像一个婴幼儿育成机,一面忙于让孩子达到各种标准,一面也在依据各种标准要求自己。在我们身边,包括我自己,所有的新妈妈们几乎都是忙乱的、疲惫的、情绪起伏不定的。我的采访对象晓晨会在网上刷到那些潇洒的母婴博主:产后不久,她们就精神饱满地恢复健身、社交,好像孩子丝毫不曾改变她们的生活,当她们怀抱着婴儿出镜时,魅力不降反增。
晓晨不知道为什么,相比她们,自己的精力会那么差,别说去健身,站不了多久她都会觉得腰酸腿疼。是哪里出错了呢?“我觉得我可能是被‘小红书’骗了。”她说。

一个新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心理咨询师宫学萍告诉我,其实,在孩子出生后的一段时间里,母亲必定有一部分活得像婴儿,甚至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母亲就是一个社会化的、有沟通能力的婴儿,她们有时候很脆弱,有时候很急躁。因为,即便婴儿离开了母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依然以母亲作为其进入人类社会的过渡体,一个表达自己的通道。
此时,母亲会自然地出让一部分自我,把孩子的需求内化,而后带着孩子的情绪将这些需求传递出来。也就是说,当一个妈妈与她的婴儿同频,她的生活、情绪都几乎不可能始终保持有序。相反,如果妈妈冷静到不能与之同频,婴儿的感受会是自己没有被接纳。而对于一个婴儿来说,妈妈是否在他人眼中能保持一个完美靓丽的形象,是毫无意义的,妈妈能否对他们的需求感同身受才是最重要的,哪怕她们经常头发蓬乱、气急败坏。
站在社会学者刘汶蓉的角度看,过去,做妈妈应该是什么样,我们只以身边的人作为参考。和身边的人比较,大家的境遇相差不多,分享的也都是真实有效的经验。但互联网的传播常常非此即彼,少有中间态度。而且,有的互联网经验不仅难以对自己真实的生活提供参考,反而会增加因比较而产生的自我怀疑、不满和沮丧。网络上经常看到的都是“最顶层”的生活方式、“最成功”的生活状态,其中不乏夸大、炫耀,也可能有商业动机。面对这样的信息,我们不免会产生一些幻想,形成心理压力,失去正常的生活节奏。

孩子被爱,那我呢?
晓晨当初想要成为妈妈,是因为抱朋友的孩子时有过一种被电流击中的感觉——太幸福了。她知道当妈妈不容易,但她以为自己需要面对的难题只有养育孩子这件事本身。
晓晨的家庭关系一直不错,当然,结婚后,她没有和长辈一起生活过。她从没有想过,孩子的出生会使家庭关系变得复杂难解,更没有想过自己竟会因为“抱孩子”这件小事,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
晓晨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孩子被月嫂、被奶奶抱着的时候明明好好的,一换到她的怀里就哭起来。她抱孩子的时间确实不多,一是孩子出生后,她先去了月子中心,回家后又请了月嫂,抱孩子的机会被“瓜分”了不少;二是如今正流行的科学育儿理念也并不提倡妈妈总是把孩子抱在怀里。月子中心的护士告诉晓晨,像她这样母乳喂养的妈妈,一抱起孩子,身上的气味就会勾起宝宝的食欲,求而不得自然就会哭,并不怪她。
但晓晨的家人不这么想。对晓晨不怎么抱孩子这件事,孩子的奶奶意见很大。她不直接责怪晓晨,而是常常对着孩子说:“妈妈都不抱你,妈妈不想要你了!”晓晨听了非常生气,但这倒也不会真的让她的内心受到伤害:“我知道我的婆婆不爱我,我能理解,我又不是她的孩子。”

真正让晓晨生气、失望和受伤的是,孩子的爸爸似乎也不觉得这样的话有什么不妥。有一次,他还郑重其事地对晓晨说:“你嘴上一直说自己很爱宝宝,可我怎么觉得你的行动和你说的话不是很相符呢?这么久了,你也不太会抱小孩。”
晓晨过去一直觉得,她的老公已经很不错了,在很多问题上,他的思想足够开放:在家坐月子还是住月子中心,喂母乳还是喂奶粉,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从不干预,全由晓晨自己决定,他只管在她的选择背后提供经济支持。晓晨记得,有一次她老公甚至对她说:如果你希望孩子随你姓,我也没问题。他也总是对晓晨说:你要先快乐,孩子才能快乐。
晓晨没想到,这样的一个人会责怪她不会抱孩子。这使她开始怀疑,他给她的自由选择,是不是他本来就无所谓,并不真的关心那些问题?在那些问题上,晓晨可以获得“自由”,但“做一个合格的妈妈”则有另一套由不得动摇的标准。
在家里,似乎任何人都有天经地义的权利去质疑一个母亲不够好。而作为爸爸呢?孩子出生以来,晓晨的先生从没有为此表现出兴奋。下班回家,如果晓晨不提醒,他甚至不会主动去看看孩子。他的理由是:我和他不太熟。他对晓晨说,孩子在你的肚子里待了十个月,你们已经培养过感情,但是对我来说,他还是个陌生人。晓晨很崩溃,好像只有自己在爱这个孩子,也只有作为妈妈的人在被要求去爱这个孩子。

有的时候,父母会以为让他们变得不开心的只是孩子。比如小花爸爸,他认为小花妈妈并不适合作为我的采访对象,她的抑郁并不具备公开讨论的价值,原因就是他们的孩子太难养了。但是多比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生完小花,多比也直接住进了月子中心,她目的明确,就是想尽可能晚一点儿地面对随着孩子的到来而升级的家庭关系。他们计划请一位常驻家中的育儿嫂,小花的姥姥和奶奶轮流来家里帮忙。
在这个计划当中,多比最担心的环节是和小花奶奶密集的相处。此前,虽然不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但婆婆也时不时地想要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传授”给儿女的小家,比如新买的牙签,使用之前她必须要一根根清洗干净。
对于生活粗枝大叶的多比来说,这简直匪夷所思。但多比从没有为这样的事情和婆婆争执过,她觉得无伤大雅,得过且过。不过,她难以想象,如果小花奶奶用这样的逻辑和标准养育、灌输小花,她要如何面对。事实上,多比的担忧不无道理。当小花开始吃辅食时,小花奶奶要求蓝莓、玉米粒都要剥皮。
除了一家人要重新磨合生活习惯,养育孩子还是一个充满了决策的过程,而每一个结果难以预料的决策都可能成为家庭冲突的引爆点。多比记得,一次小花为抗拒喝奶喊叫时,小花奶奶突然情绪崩溃,也大哭着叫道:“别再让她喝奶了,出了事儿我负责!”
事后,多比问孩子奶奶:“您能负什么责呢?”多比觉得自己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在这个家里,大家好像默认,育儿的决策权掌握在多比手里。但事实上,许多事情并非真的是由她一人决定,往往是所有成员的共同决策。只不过,当一个决定带来了好的结果时,会被认定为家庭的集体智慧或长辈的英明,而当一个决定引发了糟糕的后果,多比才会被扣上决策者的帽子,一句“你才是孩子的妈妈”让其他人都得到豁免。

其实,和孩子奶奶的种种争执和博弈虽然令人头疼、厌烦,但并不会让多比陷入难以自控的抑郁情绪。对多比来说,真正有杀伤力的“武器”握在她的妈妈手里。
多比认为,小花厌奶的情绪多半就是姥姥造成的。出生第二个月时,小花已经显现出了一些厌奶的情绪,起初她只是摇摇头躲避奶瓶,后来以大哭抗拒。那时候多比的心态还比较放松,总是说:“都哭了,就别喂了。她不想吃肯定是吃饱了。”
每当这个时候,小花姥姥就会坚定地告诉她:你不用管,她能喝。放心,我都能喂进去。退休前,小花姥姥在医院工作,基于她的职业习惯,小花姥姥始终将医生给出的建议的奶量当作死命令执行。
小花“绝食”后,多比提起自己的怀疑,姥姥的反应非常强烈:当初你怎么不坚决反对?我们只是帮你看孩子,这孩子是你的,你才是孩子的妈妈。多比不再多说,觉得争论是非对错也无济于事。但这些话会在她心底勾起久远的回想。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不知道有多少次被这样责怪,多少次争执最终都以她陷入沉默才能平息。她很害怕妈妈接下来就会说出威胁的话,“你要是……我就……”。她太熟悉这样的句式了,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你们要是不把客厅那个攀爬架拆了,我就不来看孩子了。”“你要是不能把这个问题和阿姨说清楚,那我就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了。”她知道,妈妈言出必行。从小到大,有关她的一切,最终都由妈妈决定,她几乎没有提出过反对。
作为一个新妈妈,多比总是被质疑、被责怪,而责怪她最多的人还是她的妈妈。有一次,她们一起带小花去医院检查,每每她回答医生的问诊,小花姥姥都会打断:不是这样的……她说得不对。多比很委屈,她不明白,为什么这时候没有人对她说:“你才是孩子的妈妈。”被打断的话只好变成眼泪才能排出体外。

多比的眼泪越来越多。后来,哭也不能起到发泄的作用,她关上房间门大声尖叫。再后来,她也不再需要这样的方式宣泄了。有一次,和孩子姥姥意见不合,她把自己关进房间,任谁叫她也不肯出去。她想带小花离开,不知道去哪儿,只要离开就行,或者就一直这样在房间里待下去,她感觉整个人像在另一重时空中,屋外的声音都好像来自遥远的云端。
几个小时之后,门外的一声钝响击穿了多比头顶的“云层”,有什么东西被打破了,紧接着,传来小花姥姥的尖叫:你这样,咱们大家就都别活了!
多比从这个声音中听到了熟悉的责备、威胁和有些陌生的紧张与脆弱。她忽然想起她的姥姥去世时妈妈即将崩溃的样子,也想起妈妈当时给她的承诺:“我一定能调整好自己,我要是没了,你怎么活啊?”多比知道,自己习惯服从妈妈,既是因为妈妈是一个总能为她解决问题的强者,也是因为她看透了妈妈在强势的背后是个不堪承受恐惧的弱者。
自从有了小花,在多比无数次被指责没有照顾好孩子的时刻,她都希望妈妈也能足够在意她,足够爱她。在妈妈崩溃的瞬间,多比又看到她的软弱了。多比忽然想:“妈妈还是爱我的。”
多比强迫自己振作起来,很难说我是替她高兴多一点,还是为她心疼多一点。当我和心理咨询师、《心的表达》的作者李沁云聊起这件事的时候,她说,当我们说“生孩子是一道坎儿”的时候,这句话并不应该仅仅从生理层面解读:每一个人在成为父亲或母亲后,都会回溯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这不可避免,因为孩子会时刻提醒他们自己曾经也是个孩子。每个人,无一例外在成长中会或多或少地经历心理层面的创伤,当那些陈旧的伤口被唤醒,每个人的承受力和复原力不同。当年轻的父母重新面对自己的父母,曾经被压抑的冲突,要么爆发,要么继续被默默承受。很多人希望改变自己的父母,以弥补童年所缺少的爱或关注,但应该改变、能够改变的其实还是自己。

当我有了孩子,我还是我吗?
在我的采访对象中,也有一位陷入抑郁的爸爸。是的,产后抑郁不是女性专利。根据2010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10%的新手爸爸会遭遇产后抑郁。但小河觉得,他的抑郁是不正当的。“不正当”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没有像妻子圆圆一样经历生产之痛、哺乳之苦,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孩子六个月大时,孩子的妈妈先他一步恢复了工作——她在“体制外”当老师,回到岗位上,一是为了挣钱,二是为了寻找机会到“体制内”工作,为孩子未来上学择校做打算。
小河经营的是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上班的时间可以自由掌控,但经营的状况不太稳定,有时能赚钱,有时一个月就要赔上几万元。家里人都支持圆圆出去工作,让小河在家带孩子。岳父说得直截了当:圆圆的工作更重要,也挣得多。
小河无可辩驳,但心里又有种说不出来的难受。他觉得自己完全失去了价值。
小河时不时会提出独自外出的要求——比如和朋友聚个会、去打场篮球之类的。每当这样的时候,只要圆圆表达出些许的不满,不管她的理由是什么,小河都会觉得他原本的生活因为孩子一去不返。
有时,小河也会把孩子送到父母那儿,争取些自由的时间。但他不愿也不敢频繁地把孩子交给孩子奶奶——和他们相比,她简直太爱抱孩子了,抱到腱鞘炎、颈椎病发作也不愿将孙子放下。对自己的妈妈,小河无奈又心疼。每当孩子被奶奶抱了一整天,回家以后,小河和圆圆就要花两三天才能把孩子调整回轻松好带的自主入睡模式。而一旦哄睡孩子的事影响了圆圆第二天的工作状态,小河又会陷入对妻子的歉疚中。小河夹在妻子和母亲中间不知如何调和。

有几次情绪冲到头顶,他竟无法自控地以极端的行动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无奈——他要跳楼,站在窗口让圆圆在他和孩子中选择一个。他说他时常会觉得,如果没有了孩子,他和圆圆之间就不会有矛盾,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而情绪平息后,他又会陷入深深的自责,觉得如果没有了自己,那一切问题才真的能够解决。
小河没有发现,或许并不是他的抑郁不正当,而是他所认为的不正当性使他抑郁——在他的意识中,一个丈夫、爸爸,不能出去工作是极其不正当的,与此同时,带孩子这件事是毫无价值的。
养育新生的孩子像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它责任重大;另一方面,把一个婴儿养大、养好,又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一个优秀的养育者,也只是一个合格的养育者,人们并不认为她和他创造出了价值。
心理咨询师宫学萍提到,过去谈到产后抑郁,主要原因会归结为生产痛、身体虚弱、激素不稳,人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心理能量一定是很差的,但现在,产后抑郁与养育者自身获得的价值感低有很大关联。
在她的印象中,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亲子课、育儿书卖得特别好,当时,养育的价值被绝对肯定,父母的作用曾一再被强调,而现在,“不育保平安”是常常能听到的声音。如果一个人把时间全部投入到养育孩子这件事,简直亏大了,养孩子与和客户谈生意相比,似乎总像是损失了几个亿。抚育观念和价值在对立的声音中两头摆荡。“如果一个时代认为抚育幼弱都没有价值,那身在其中的每个人走在人生的两端时该怎么活呢?”
我问小河的妻子圆圆:他这样闹,你呢?圆圆说:如果我的情绪再不稳定,那日子只能别再往下过了。
但她也确实在很多时候感到不平衡:我挣得多,我的工作可以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我就该在别人产假都还没歇完的时候出去工作吗?我也很想在家陪孩子。下班回来看到孩子,我总是觉得很愧疚,觉得自己陪他太少了。可是忙了一天,进门就要开始带孩子,我又实在是太累了。

圆圆时常想,怎样算是一个真正好的父亲呢?她想,小河已经是个不错的爸爸了。她身边的家庭中,孩子们的爸爸几乎都是完全隐形的。她经常从朋友口中听到:“我孩子的爸爸已经不错了”,那通常是在说一个上班挣钱养家的父亲,或是愿意陪孩子玩一会儿的父亲,或是能知道孩子吃什么牌子奶粉的父亲,或是在孩子大哭的时候,即便他袖手旁观,但至少不会怪罪孩子妈妈的父亲——往往只需要一条,一个父亲就可以轻松地跻身好评榜。
但是好妈妈呢?圆圆想,这些都加起来够吗?远远不够。在家里,圆圆负责赚钱并不是出于她本人对事业的追求。没有做妈妈的时候,她安于做“编外”老师:时间自由、没有压力。可孩子出生还不到半岁,家里就迅速陷入了择校焦虑——去哪儿上学更好?要不要换学区房?最终,大家一致认为圆圆应该去参加考试、努力进入足够好的“体制内”学校工作,这样孩子上学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圆圆也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案。但这就是一个足够好的妈妈吗?她并不这样认为。为了换工作,她需要做的是挤压休息的时间备考——她不能再减少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了,“我不能只给孩子一个好学校,他现在更需要妈妈的陪伴”。
圆圆所要承受的,是“优绩主义”和“成为无微不至的妈妈”的双重挤压。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成为妈妈,意味着需要在所谓独立女性和传统女性叙事之间做选择,事实上,并没有选择。在今天的社会期待下,一旦成为母亲,放弃职业会失去安全感,而减少对孩子的陪伴则会被无尽的愧疚感填满。
我想起我的另一位朋友。她在讲述她坐月子的经历时,忍不住痛哭起来:生完孩子还不到一周的时间,来照顾月子的婆婆就要求她给孩子手洗衣服。婆婆抱着孩子站在一旁观看,对着怀里的孙女说:“你看,妈妈是个独立女性,让妈妈给你做个榜样!”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31期封面故事)

排版:小雅 /审核:雅婷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大家都在看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4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6137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