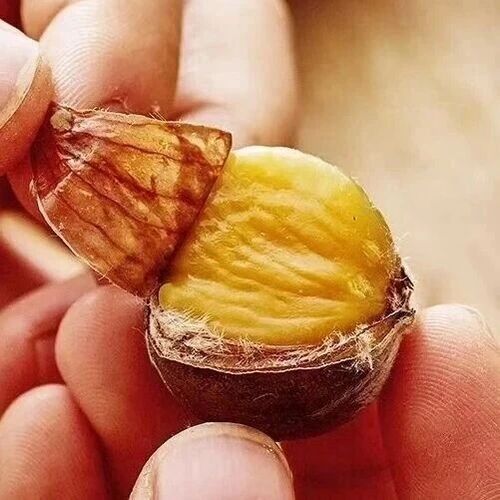要到多少岁,才能走出愤怒父亲的阴影?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10-14·阅读时长24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主笔|薛巍
“一个稳重、体面的中产之家”
“一个稳重、体面的中产之家”
“一个稳重、体面的中产之家”
有些作家的经验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但父子、兄弟之间反目成仇的也不少。《泰晤士报》9月12日的一篇文章说:“在英国,家庭决裂现象相当普遍。有一份报告显示,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受到关系疏远的影响。因此,温莎王室在面对这种状况时并不孤单。本周哈里王子与国王共进下午茶,这是他自去年2月以来首次与父亲见面。”
专家表示,和家人的关系破裂后,不必强求和解。“如果你无法原谅别人,那没关系,但也要原谅自己,否则你会背负羞愧和内疚。宽恕很重要,它能让你内心平静。”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出生于1968年,从小受到他爸爸肉体和心灵上的折磨,他一直巴望着自己的爸爸死掉。在他29岁时他爸爸病逝了,他表现得很冷漠,他甚至认为,“爸爸活该死,他死了是好事”。

随后他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自己的婚姻出了问题,甚至一度想自杀,到他40岁时,他开始写《我的奋斗》。这本自传体小说共6卷、3000多页,该书出版后他被誉为挪威的普鲁斯特,在挪威几乎每10个人就买过一本,他也受到了詹姆斯·伍德、扎迪·史密斯等英美评论家和作家的好评。
《我的奋斗》的出发点和核心都是奥韦和他爸爸之间的斗争,“父子关系的复杂性——其中交织着嫉妒、失望与过度认同——是《我的奋斗》的核心所在”。
奥韦算是成长于一个中产家庭:他爸爸是一位语文老师,妈妈是精神科护士。16岁时父母离婚,之后他的爸爸因为愤怒和郁郁不得志而开始酗酒,一步步把自己喝向死亡。
《我的奋斗》一开始最让人感到震撼的就是,奥韦在他爸爸去世后一点也不感到伤心,虽然他时而会痛哭。在他爸爸去世六个月前,一位亲人打电话问奥韦,他能不能去照顾他爸爸,他回复说:“我不想照顾他。他可以照顾自己!我一点都不想要他。”

当时奥韦28岁,跟妻子住在卑尔根。半年后,他哥哥英韦打电话告诉他,他们的爸爸去世了。
“这是一件很大的重要的事,它应当完全占据我的全部身心,但它没有。”挂上电话后,他在卑尔根的公寓里打开水壶,等水烧开。“我就站在这里瞅着烧茶的水壶,心里恼怒着为什么水还不开。”他试图给爸爸的死寻找某种意义,但没找到。“他的死没有意义。”接着,他突然感到一丝高兴,因为想到自己或许能继承一点钱。“他有钱,应当是有钱吧⋯⋯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把这钱都挥霍了吧?”
奥韦的爸爸去世时才56岁,他生命最后的几个月一直和他年迈的母亲,也就是奥韦的祖母住在一起,两人都嗜酒如命。当奥韦回到他儿时熟悉的祖父母家时,眼前的景象令他震惊。到处都是空酒瓶,空气里弥漫着腐烂的气味。味道来自一大堆毛巾和旧衣服。而那曾是“一个稳重、体面的中产之家”。
令人恐惧的父亲
令人恐惧的父亲
令人恐惧的父亲
奥韦写完《我的奋斗》的第一部《父亲的葬礼》后,把手稿寄给亲戚看,有的看了之后感到伤心和愤怒,尤其是他叔叔。“他们说关于他父亲的描述是不真实的——他没那么邪恶,也没那么酗酒。他是个好父亲。”

事实上,在他的记忆里,关于他爸爸比较温馨的回忆只有两个:在他家的地下室,他还能看到爸爸拿粉笔写下的给他取的绰号,“那是我们刚搬进去的时候,样样事他都乐在其中。那些名字还在。小傲伟,乐韦,爱韦,可爱韦,快乐儿可爱韦”。
还有一次,奥韦手上长了些疣子,他爸爸说,用培根涂抹手指头,然后到花园去,把培根埋在土里,那些疣子过几天就会不在了。“它就有这么奇妙!疣子真的会不见。只等着看吧!把爪子伸出来。”给他涂抹过之后,他手里拿着一把铁锹,开始铲土,然后把培根放进去了。
其余的呢?
他曾经反复狠狠地欺凌过他。就因为奥韦多吃了一个苹果,爸爸就逼迫他接着吃苹果。那时,奥韦想象在另一个他已经长大的世界,“我可以攥紧拳头,狠狠地揍他的鼻子一顿,让他的鼻梁破裂,鲜血长流。或者更好的状况是,断裂的鼻梁骨扎进了他的脑里,让他一命呜呼。我可以把他朝墙上压过去,把他从楼梯上扔下去。我可以揪住他的脖子,把他的脸摁压在桌面上”。

老克瑙斯高总是随意地把对孩子的惩罚扩大化,很少就事论事。奥韦挺喜欢去学游泳,因为游泳之后有“让人感到温暖的、长达半小时的淋浴”,以及“戴上游泳帽和护目镜时,像是被封闭起来的感觉,尤其是在游泳比赛的时候,那时我有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泳道,它在入水台下等待着我”。但有一次,奥韦去游泳时,把袜子弄丢了,他爸爸发现后,“狠命地钳住了我的手臂,把我往墙上压⋯⋯他揪住我的耳朵,一个劲地拧着”。他还责骂道:“你究竟多大了?你以为我们有多少钱?你以为我们有钱给你买你弄丢的衣物?”“你这个混账东西!”“你要保管好自己的东西!”“不准再去游泳馆了⋯⋯今天晚上没你的饭。你可以直接上床了。”
老克瑙斯高也从不考虑孩子的处境,听他们解释。有一次奥韦帮他外公打开电视机,发现电视机坏了,他知道,在家里他们是不可以自己开电视机的,爸爸肯定会打他,“我走进我的房间,恐惧地打着寒噤,胃里翻滚起来”。他想起哥哥挨打的情景:爸爸得知英韦和邻居的孩子打架后,“英韦手里拿着一本杂志躺在床上,这时候爸爸走进去,猛地一把拽起他摇晃,把他在两堵墙之间掼来掼去”。

有一次,奥韦和小伙伴帮助一位老太太拔掉一棵树,为了表示感谢,老太太给了他们一枚五克朗的钱币,他们用这枚钱币买了糖果。到了家里,奥韦把糖果藏在了被子下面,还是被他爸爸发现了,立刻质问他:“你这糖果是哪儿来的?你是从哪儿弄来钱买这些的?”奥韦据实回答说:“一个老太太给我的钱!”他把耳朵拧得更紧了,“为什么有老太太要给你钱?”“你对我撒谎了。是不是?”
最后,他爸爸假装给当事人打电话确认,然后说对方说没这回事,并命令他把糖果扔到垃圾袋里。在他假装打电话时,奥韦说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奥韦说,他和哥哥对他们的爸爸怀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小时候的奥韦经常因为害怕而落泪,“我是那么地惧怕他,以至于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法建立起对他的感情;对于他的情感打我出生以来就从未有过,对他一次也没有过亲近的感觉⋯⋯他一走进厨房,我们立刻静默,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好像我们在专心专意地用餐;相反,要是他走进客厅,我们就继续聊天”。

小时候,在家里,他时刻关注着爸爸的动态:他在楼梯上的脚步声,他是不是正在去找他的路上?“他眼睛里的野蛮⋯⋯他的愤怒如狂潮,席卷整个房间,向我冲来,击打着我,击打,击打,然后再退撤而去⋯⋯突然间他就会勃然大怒。他揍不揍我其实不打紧,这跟他拧着我的耳朵转一圈,或狠狠地钳住我的胳膊,或是把我拽到某个地方,看看我都干下了些什么其实没什么区别,我怕的不是这些皮肉上的疼痛,而是他,他的声音,他的面孔,他的身体,他所喷射的狂怒,这是我所害怕的,我永远无法摆脱这种恐惧,它深深地嵌入我整个的童年时期,嵌入了我的每一天里。”
爸爸对他的“教育”导致奥韦变得非常脆弱。他说:“作为孩子,最重要的是被接受和被爱,而如果你总被批评,你就会觉得自己有问题——这可能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关乎自尊,关乎你是否喜欢自己,而我并不喜欢自己。”
《在夏天》一书中,奥韦在2016年6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问他想不想见当时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他说不想,“为什么我一想到要见他就浑身发冷?权力、名声、对人性的蔑视?是的,都有,但主要是他的专制。以我对权威的恐惧,我想象不出比这更可怕的遭遇了。我会不会试图讨好他?会不会为了让他喜欢我放弃我信仰的一切?很不幸,会的”。

爸爸就曾经是家里的国王。奥韦说,他爸爸认为生活中非必需的活动统统都要去掉:驾车出行时尽可能快地开车,从一个地点到达一个地点。吃饭是因为我们必须得吃;看电视的时候,就看电视,不能够讲话或是做其他的事情;当我们走进花园,我们就必须得走在石板上,不能在草坪上面走,也不能在上面跑,更不能躺在上面。
更不近人情的是,爸爸从来没有在家里给他们开过生日宴会,认为没这个必要,晚餐后跟家里人共享一块蛋糕就足够了。孩子不可以带自己的朋友进屋,因为他们待在屋里只会添乱,把屋里搞得乱七八糟。他的任何工具孩子都不许碰,像锤子、螺丝刀、钳子或者锯子、雪铲或雪刷,两个儿子也不被允许在厨房做饭,不能自己切面包片,也不能自己开电视机或是收音机,因为那会让屋里的东西不翼而飞,搞得乱七八糟,只有他或是妈妈才能动用所有的东西。
走出父亲的阴影
走出父亲的阴影
走出父亲的阴影
老克瑙斯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新成员,对这个大千世界信息灵通。他为什么会动辄打孩子?为什么那么容易愤怒?是因为孩子特别不好管吗?并不是。奥韦小时候确实有点顽皮,但也都算是正常的程度。他曾经跟别的孩子一起,向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扔石头;他没打招呼就把爸爸新买的铲子拿走去帮人铲雪挣钱了;他和一个朋友放火烧了树林。
奥韦推断爸爸之所以虐待他,是因为爸爸小时候也被他爸爸打过。“他就是这样被教育的,充满了愤怒和惩罚。他的母亲情绪非常不稳定,父亲又很严厉。”

奥韦的哥哥英韦敢于反抗爸爸的欺凌,比如爸爸要换一个学校工作,他都拒绝跟着转学走。奥韦则是爸爸越对他不好,他越想努力地取悦他。
老克瑙斯高40岁离婚后开始酗酒。奥韦自己则是早早染上了这个毛病。15岁时他就体会到:喝酒真是太爽了。“那年夏天我十六岁,当时想做的只有三件事。第一件是找个女朋友。第二件是和某人睡觉。第三是喝醉。”“一如既往,酒精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自由和幸福,它把我送上潮头,那里一切都很美好,我唯一真正的恐惧就是落潮,它绝不该结束,为此我只能不停地喝更多的酒。”
不过,奥韦小时候的经历并没有毁掉他。《纽约时报》的书评人德怀特·加纳说,《我的奋斗》的前三卷让人觉得“奥韦是个很爱哭的人,生活总能触动他,你几乎会忍不住想递给他一盒纸巾”。但《纽约客》的编辑约书亚·罗斯曼说,奥韦其实挺顽强,“他父亲的愤怒就像是海浪,奥韦很早就学会了看见浪头的来势,做好准备,迎着浪面往上游,希望能在浪头卷住自己之前潜入水下。如果没能及时下潜,被浪打翻、拖入水中——他就在那里,等待下一道浪的到来⋯⋯对他来说,生活就是一场斗争,这场斗争既折磨人又有益,既英勇又悲壮,既充满活力又一成不变,既有意义又浪费时间”。
小时候挨打的经历让奥韦下定决心以后自己要做一个好爸爸,“我活着,现在我有自己的孩子,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试图做到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不让他们对他们的父亲感到恐惧。他们不害怕我。这我知道。当我走进房间时,他们不会畏缩,他们不会垂下眼睛看着地板,他们不会一有机会就尽快溜开”。

《我的奋斗》被认为是一部没有什么重要的故事情节的小说,与之相似,王朔1991年创作的《我是你爸爸》也是理念多过故事。此外,这两本书还有其他相似的地方:写的都是父母离异的孩子,他们的爸爸都是文化人(王朔笔下的马林生是书店店员);爸爸都怀疑和痛恨自己的孩子撒谎,都会动手打孩子(“儿子马锐从小到大所经受的暴力袭击,除了一小部分发生在同伴之间,最悲惨最屈辱的几乎全来自他这个父亲”);儿子都特别畏惧他们蛮横、狂暴的爸爸(“他一见马林生就显得瑟缩、沉默,他们的家庭蒙上一层阴郁的气氛”)。
不同的是,马林生的儿子马锐挺早熟,特别懂人情世故,还敢跟他爸爸斗斗嘴。马林生突发奇想,做了一次处理父子关系模式的革新,说要跟儿子平等、真诚相待,对儿子说可以喊他“老马”,但这场实验好像因为过于理想化而失败了,对于失败的原因,他的邻居夏青的妈妈的一番话说中了要害:“在孩子面前该装还得装,不能太让他们看透了你⋯⋯没人需要你的真诚,包括你的孩子。”也就是说,对孩子既要温情,又要有权威,既爱他、顺着他,又要他听话、服管,这很难两全。不是所有父亲都有这样的智慧。

美国导演贾德·阿帕图说:“当爸爸并不容易。我们竭尽全力想把孩子养好、不毁了他们,却鲜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困难之处在于,我们自己是由同样一头雾水的父母养大的——他们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于是,即便我们迫切地想要终结某种恶性循环,也早已带着创伤,不清楚该如何改变。结果呢?我们还是会把孩子搞得一团糟——最理想的情况,也不过是把他们逼到要报复,方法就是活得比我们更成功、更快乐。”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第39期)

排版:球球 / 审核:雅婷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大家都在看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1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6158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