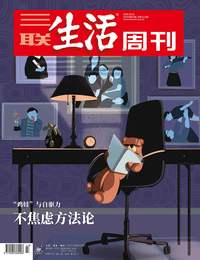处女作之后,第二部电影是道坎?
作者:宋诗婷
2020-10-21·阅读时长7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3939个字,产生0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电影《蓝色列车》 剧照
处女作光环
“你觉得,老马和小伟能认识吗?”
“不能吧,老马太不爱说话了。”
“我觉得能,越是这样边缘、孤独的人,越能瞬间走近。”
平遥影展的采访间里,导演张大磊提起电影里的人物,就像在聊那些相识多年的老友。“老友们”生活在一个叫“库村”的地方,那是中俄边境上的一座小城,萧条、寒冷,冬天的马路上总盖着融化不掉的雪。苏联建筑和庞大的工业遗址构建了小城的空间,一列蓝色火车载着孤独、笨拙的人来到小城,寻找往日时光,或者带他们离开库村,追赶更扎实的生活。
“库村”存在,但也不存在。张大磊在俄罗斯念大学时,宿舍在圣彼得堡郊区,一个叫库布齐那的地方,大家都管那叫“库村”。因为过于偏僻,在谷歌地图上都搜不到“库村”。宿舍楼只有孤零零一座,楼对面是一片森林,冬天极昼时,一帮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就在户外喝酒、吃烤肉。
张大磊挪用了“库村”这个地名,但除了名字,电影里“库村”的一切都是虚构的。“《八月》的空间是我现实中的故乡,《蓝色列车》里的库村就是我的精神故乡。”如果一定要把《蓝色列车》和前作《八月》挂上点联系,张大磊愿意这样解释。
在导演不断描述和解释“库村”的故事时,《八月》被反复提起。《八月》是张大磊的长片处女作,2016年,这部以导演的童年经历为创作素材的电影拿到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影片大奖。尽管业内评论说,当年的金马奖是少有的“小年”,入围作品整体偏弱,但处女作就问鼎金马,张大磊在导演这条路上的起点实在太高了。
那几年,张大磊不是唯一一个起点高的导演。2015年前后正是电影圈资本膨胀、业内热情拥抱新导演的几年。张大磊之前,毕赣以一部几十万元成本的《路边野餐》被艺术电影圈接纳,成为金马和戛纳的宠儿。再早些时候,忻钰坤的小成本电影《心迷宫》让观众看到了新一代导演开拓类型片市场的希望。文牧野和《我不是药神》的成功,更让华语电影开始迷信青年导演。

导演张大磊
一战成名后,压力和资本全来了。这些年轻导演的第二部电影都无一例外地拥有了比第一部电影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投资,配置了至少是观众看着脸熟的明星。加码的投资和更高规格的演员配置能客观上提升电影的制作水平,但不可控和成本回收的压力也随之而来。
因毕赣的第二部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采访他时,他曾提到,第一天坐在监视器前,整个人有点懵,在那之前他从未在拍摄过程中使用过那东西。这还仅仅是一个小细节,因为缺乏经验和与各部门的磨合,电影的整个拍摄过程一度更换过美术,拍摄暂停、超期、超支,到了后期宣发阶段,因为片方急需回收成本,还闹出了过度营销的负面评价。尽管《地球最后的夜晚》依然是入围了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也拿到多项金马奖提名,但电影整体评价远不如处女作《路边野餐》。
对于一战成名这件事,忻钰坤有过自己的态度,接受采访时他提到,处女作是块敲门砖,面对导演的第一部作品,观众会宽容地为他们垫上一个箱子,到了第二部,大家会把箱子抽走,这时候作品质量和口碑如何,就是纯粹的能力问题了。
这“能力”包含专业上的技能,也考验导演驾驭团队的能力,更难把握的可能是在拥有了更好的资源后,不得不在创作自由和商业回报间寻找平衡的能力,任何一方面把握不好,都可能导致电影失控,或导演的自我迷失。
张大磊就是在这样的优势和压力下开始第二部长片《蓝色列车》的创作的。
文章作者


宋诗婷
发表文章218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839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