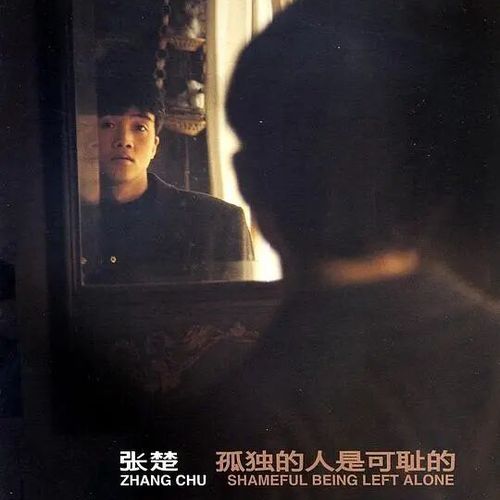面对“脆弱”,我们还能善始善终吗?
作者:读书
2021-03-24·阅读时长14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7147个字,产生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张宝明
一
“好人不可能被伤害。”(Nothing can harm a good man either in life or after death)这句话出自苏格拉底,由柏拉图对话集的《申辩篇》给出出处。对此,玛莎·纳斯鲍姆阐释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要保障了美德,那么也就保障了有关生活的一切东西。”(《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修订版序言 ”2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应该说, “好人 ”会不会受到伤害是一个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善的脆弱性》也就探讨了这样一个主题:“人类容易受到各种运气的影响 ……本书关心的是运气在好品格的形成中的作用,但它关注的焦点是做个好人和过一种欣欣向荣的人类生活——典型地包含了美德活动的那样一种生活——之间的差距。”(同上)尽管作者在修订版序言中特别强调了 “运气 ”与“随机性 ”以及 “因果性 ”的无涉,但其“人类行动者缺乏控制的事件 ”之表述却对 “运气”硬核蕴含的不确定性、偶然性与 “无厘头 ”给出了定义。由此出发,我们油然而生一种预设:在“好人 ”与“好运 ”,“美德 ”(品格)与“运气 ”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吗?进而言之,好运总会偏向具有美德的好人(君子)吗?
纳斯鲍姆以一咏三叹的口气反复提示读者:
“本书一个中心议题一直是,人类雄心勃勃地力图通过艺术或科学来征服和支配运气。”(320页)尽管人类为此的努力充满艰辛并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还是 “苦”此不疲。这一切,都折射出自从盘古、亚当以来的人类面对世事沧桑以及由此带来的命运多舛,是何等渴望将幸福妥妥掌控在自己手中的心路历程。膜拜各类图腾、祈福于各类巫师并皈依于各类宗教的仪式,中外概莫能外。随着文明曙光的到来,对以理性为主体的知识、技艺、科学的追求前赴后继。而这一切又都建立在人类在大自然前何等无知、渺小以至于非常脆弱的认知之上。
这一认知早在古希腊时代的《俄狄浦斯王》《阿伽门农》《安提戈涅》中就有了写照。就理性本身而论,其价值本身就存在着无法归类的多元性,而与之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伦理要素 “善”也有着无法还原的多样性。如此一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形无处不在,每每渗透在我们生活的角角落落。当然,无论是在戏剧中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都会有一些看来法不责众的选择。而且这些选择不会招致致命的非议,譬如:“没有哪个有头脑的人,会指责亚里士多德的船长,丢掉船载的货物来拯救他自己和他人的性命,即使他在合同上有义务保护这些货物。”这不但在古希腊悲剧中,即使在二十世纪那部电影《泰坦尼克号》上都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毕竟,人类还有更为复杂的情境需要面对:“如果唯一拯救海船的方式就是他把自己的妻儿扔进海中,那么情形就会大不同了。”(35页)伦理中的道德冲突会达到一个极致状态。在责任和义务之间,会有一种人性撕裂的刻骨铭心。当阿伽门农以献祭自己的爱女为代价换取远征军前行的许可证之后,他的命运也由此彻底改变。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不能不一个人担当。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死结在于,“选择总是意味着几种可能性之间的选择;对行动者来说,他可以选择所有可能性的概率不高。但是在这种特殊处境中,尤其痛苦的是没有哪一种选择是良性的 ”(44页)。
面对理性价值多元对立,任何 “简单化 ”取舍都必然陷入无法排解的窘境。在个人与城邦、信仰与爱情、理性与情感等编织而成的人类社会中,这一复杂和纷繁在《安提戈涅》中演绎得也同样深刻。对见了棺材才落泪的克瑞翁来说,只有经过失去爱子并发生家庭毁灭的悲剧后,他才认识到城邦不是单纯的善,也不是唯一的目的。他撕心裂肺的悔恨是对其 “慎思的狭隘和贫乏 ”。要知道,“单一标准,把许多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排除在外,从而成为极其贫乏的标准 ”(82页)。针对这一由来已久的 “悲欢离合 ”与“阴晴圆缺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无奈之下曾经给出一条不是答案的答案:当一个年轻人必须在加入法国抵抗组织的爱国主义义务与赡养其年迈的母亲之间做出选择时,“最好的出路是彻底放弃这些准则,自由地、清醒地以及无悔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20777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