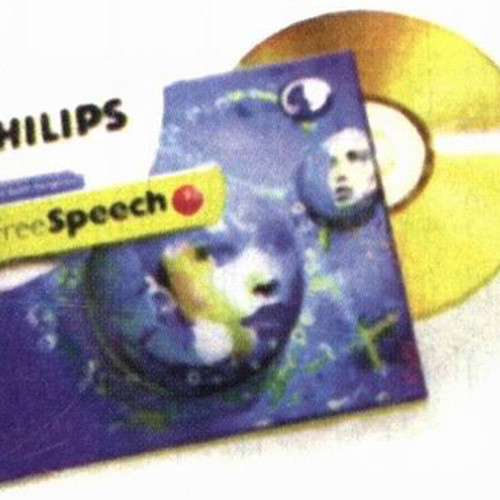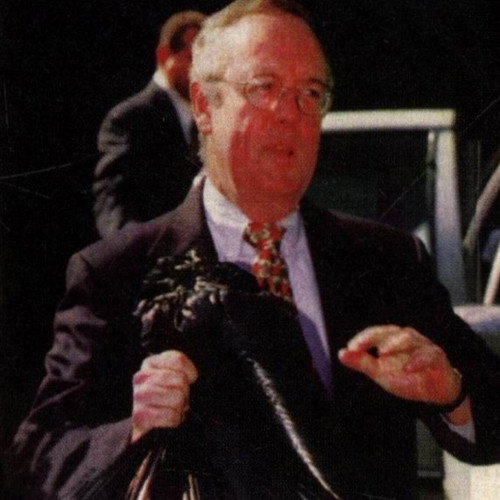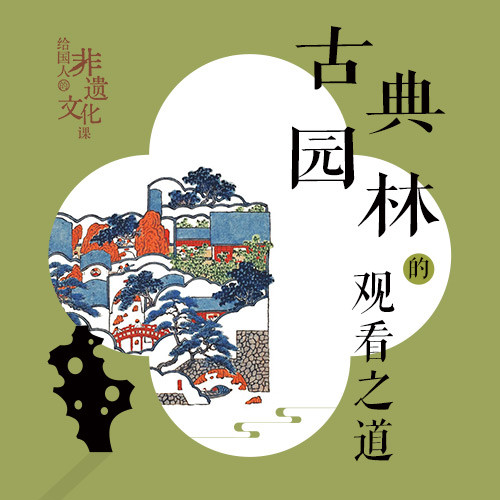浮城偷生记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2018-02-24·阅读时长16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8016个字,产生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 法国电影导演、现代派艺术家、诗人让·谷克多
)
耻辱的和平?
“清晨的天气好极了,昨晚的暴风带来了清新的空气,鸟儿们在天空鸣叫,一切和蒙彼利埃一样,这也是我必须佩戴黄色大卫星标志的第一天,现在生活有了双重面孔,一面是包容在这迷人清晨中的青春和新鲜感,另一面是这标志代表的野蛮、邪恶与破坏。”1942年6月8日,21岁的犹太籍索邦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学生海伦娜·贝尔在日记中写道。同一时刻,在巴黎左岸混迹的23岁青年画家菲利普·朱利安也开始了自己的一天:“清晨,阳光斜斜地投射进房间,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真让人手不释卷,凭窗而望,不仅浮想联翩。稍晚,与克莱西、格雷迪共进午餐,在书店中购得新版里尔克诗歌集一部,感觉不过尔尔。”
两段日记同样充斥着巴黎布尔乔亚阶级悠闲的情调,实际上,自1940年6月14日后,两个艺术青年的生活轨迹便形成了两条永不相交的曲线。“60年来,法国的战败和沦陷时代,仍然是个充满争议和令人困窘的话题,这段被让·谷克多称为耻辱和平的年代,直至今日,仍然制造着某种微妙的倒错。”纽约巴德大学亨利卢斯人权与新闻学专业教授伊安·布鲁玛对本刊记者说,“艺术、文化生活,似乎是法国军队放下武器后,它拥有的唯一保持自身尊严的武器。然而在何种程度上,法国艺术家该为自身的创作活动负担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是个高度争议与难以量化的问题。身为战胜者之一的法国人,较之德国,更难以鼓起勇气去探寻这一段历史的真实细节和脉络。”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
发表文章6068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48000人
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