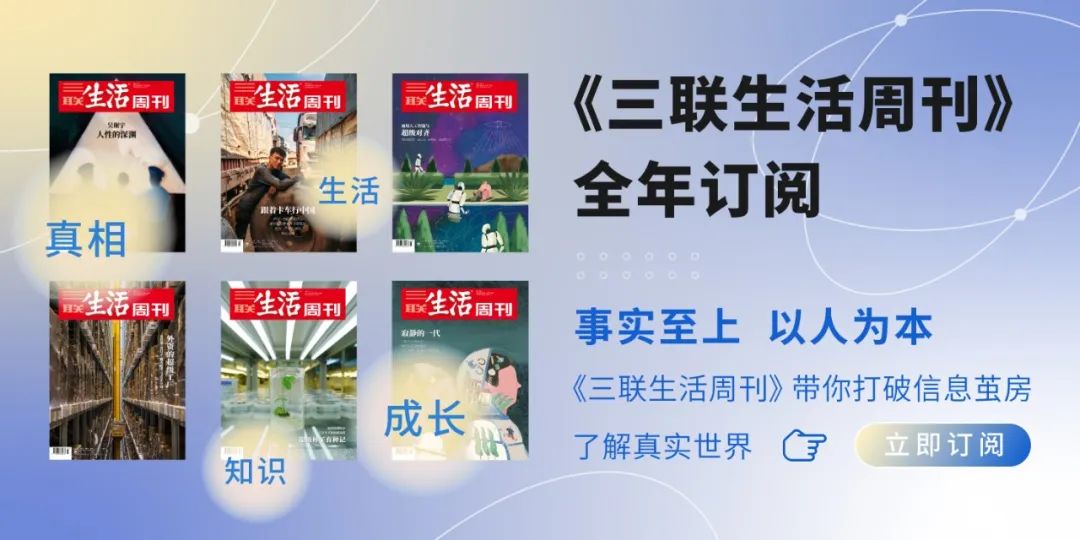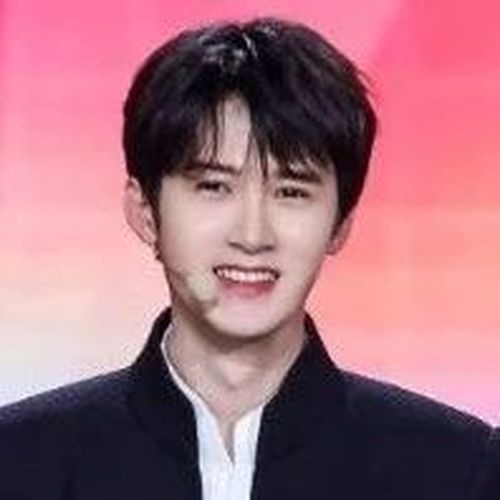第一人称的晚年独居观察|专访上野千鹤子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今天·阅读时长24分钟
20多年前,上野千鹤子在日本山梨县八岳南麓购置土地,建起别墅。疫情期间,她将这栋度假别墅转为主要居所,生活重心从都市转向山野。那一年,她年过70,正从日本医疗制度划分的“前期老年人”迈向“后期老年人”阶段。这段生活,不仅意味着环境的切换,也是人生阶段的过渡。
2023年,上野千鹤子将山居期间的生活随笔结集成册,出版了《在八岳南麓,直到最后》(以下简称《八岳南麓》)。这位一向以锐利、强悍著称的社会学家,在书中展现了更私人、更温柔的面貌——用第一人称的叙事,加上社会学者的观察力,忠实叙述自己在老年生活中的探索与困惑。
在本书中文版出版之际,我们与上野千鹤子进行了线上对话。镜头对面的她并不在山中,而在东京。她邀请我们一起,为线上会议挑选一张合适的虚拟背景。她在几张照片中切换,并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她自己在八岳的住所中拍摄的。
她最终选中一张树木葱郁的照片。“因为有季节感,”她笑着说,“城市生活的便利无可替代,但自然生活也很重要,所以关于在哪里度过晚年,我依然在犹豫中。”
 2024 年 10 月 1 日,东京的公园内老年人正在晨练
2024 年 10 月 1 日,东京的公园内老年人正在晨练
上野千鹤子对老年话题的关注可以追溯到近40年前。38岁时,她在论文《老年问题与老后问题之间的差距》中,提出应当将老人当成主体而非客体来研究。这种“主体”意识贯穿她的老年问题研究始终。此前的著述中,她一直标注着自己的年龄:50岁时,她意识到自己从年龄上已经“越过巅峰”,开始“向老而生”。58岁,她开始写“独居者”三部曲,从自己独居者的身份出发,讨论如何一个人度过晚年。写完三部曲后,她开始接近身体衰退的“摇坠期”,期待进入65岁成为“需护理老人”,那样便能以当事者的身份发言。《八岳南麓》终于实现了她一直以来的愿望。
翻开这本书之前,我一直抱着好奇的心态:此前所有的理论准备、社会调查,在她自己的生活中能提供帮助吗?对老年生活进行过周全思考的她,能顺利实现自己的设想吗?对于一个人的老年,她的心中仍会存有疑虑吗?
八岳南麓是一片充满野趣的居住区。上野千鹤子在这里找回了自然时间的节律感,第一次“无为地享受时间流逝”。但山间生活自有它的不便利之处。对于其中的种种懊恼与妥协,上野千鹤子并不讳言,那些小小的抱怨、理想和现实的落差,看起来真实而富有趣味,更可以为有类似打算的人们提供参考。
比如当你拥有一块土地,到底要成为“园艺派”还是“家庭菜园派”?上野千鹤子和朋友租地尝试种菜,最终因惰性与杂草败下阵来,只能当个“园艺派”。又比如偶然来拜访的野生动物,它们固然可爱,但也会破坏人类种植的花草与作物,该如何处理?山中的人们多半只能将鹿、野猪拦在门外,顶多喂喂野猫。与自然共处,看似美好,实际充满了矛盾和妥协。
更多的妥协发生在身体与心理内部。老年不是一个时间节点,而是一段不断踏入深水区的过程。50岁时,年龄只是一个数字,上野千鹤子尚且觉得“时间的流逝没有显见的节点,我自己也并没有出现特别变化的分水岭”。70多岁,身体的衰老已经成为日常可感的事实。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IC Photo 供图)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IC Photo 供图)
一向喜爱登山和滑雪等户外运动的上野千鹤子,开始感觉到膝盖出现“不祥的感觉”。站在滑雪场上,她开始思考眼睛、腰、腿还能听使唤多久。一直享受驾驶乐趣的她,也逐渐到了要接受“高龄者培训”的年纪,再过几年,就要作为“后期高龄者”接受认知障碍测试。至于能不能等到自动驾驶成熟的那一天,她不抱太大希望。于是,上野千鹤子去观察一位放弃驾驶的女性的生活,发现也可以用每周租车、集中外出采买来解决。接受自己的局限,在妥协中寻找新的平衡点,也是老年生活重要的一课。
独居并不意味着孤独,相反,人际交往的水平决定着老年生活的质量。在八岳,移居者们组成的“猫之手俱乐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团体。人们利用自己掌握的实用生活技能互相帮助,建立起深厚的友谊。“猫之手俱乐部”里,做饭、木工、开车等技能比陶艺、绘画、唱歌剧更受欢迎。为避免帮忙变成负担,他们还创造了象征性交换的“喵券”,维持人情又不生尴尬。这种微妙而细腻的互助方式,唯有亲历者才能体会。
在日本学术界,以上野千鹤子为代表的一群学者,一直关注着“如何独自度过老年”这一话题。这个提法如今是日本社会普遍接受的现实,背后的社会变迁引人注目。
如上野千鹤子在书中列举的数据:2007年日本独居老人比例为15.7%,到2019年激增到27%,加上两位老人单独居住的33%,加起来超过半数。2000年,和子女居住的老年人比例接近一半,到2017年,这一比例下降到30.9%。过去十几年,“父母和孩子分户居住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
日本医生辻川觉志则在他的著作中总结了决定老年生活满意度的三个关键: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拥有真正信赖的朋友(亲戚),以及随心所欲的生活。他对各种不同境况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做过调查。其中一条结论是,“没有子女的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最高,烦恼度低,觉得寂寞的比例低,觉得不安的比例也低”。
如果跳出传统思维的框架,“独自度过老年”不一定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也可以是自发的选择。在如今的中国人看来,“一个人终老”的图景还是难以接受。日本学者的讨论,或许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将来更有参考意义。如果年轻时选择不结婚不生子,或者选择逃离不健康的家庭关系,老年就必然孤独凄凉吗?答案可以是多样的。
 2023 年 7 月 4 日,85 岁的大岛安武(Yasutake Oshima)在位于东京近郊神奈川县茅崎市的家中进行拉伸运动(视觉中国 供图)
2023 年 7 月 4 日,85 岁的大岛安武(Yasutake Oshima)在位于东京近郊神奈川县茅崎市的家中进行拉伸运动(视觉中国 供图)
如何迎来死亡,是“一个人度过晚年”必须解决的终极问题。在这本书中,上野千鹤子记录了她照顾好友历史学家色川大吉,陪他走过最后一段人生路的过程。得益于介护保险制度、走访介护、定期巡回的医疗服务,加上有好友上野千鹤子的帮助,色川大吉得以在自己家中迎来人生终点。遗憾的是,在法律规定的限制下,身为“介护保险使用监护人”的上野千鹤子,在代为处理色川先生的个人事务时仍然遇到重重阻碍,最终无奈选择了通过婚姻登记获得法律上的权限的方式。
在本次采访中,她回应了这个当时引起争议的事件。语气带有遗憾,但是非常坦然,“我败给了日本的家庭制度”。要想让更多人获得如何老去、如何告别世界的选择权,仅仅改变个人观念和社会偏见是不够的,还需要一整套制度体系的支持。
我想知道,上野千鹤子对于自己的人生终点,是否已经有足够的安排?能否得到可靠的协助?能否按照自己的意愿告别人世?她对这些问题有信心吗?我以为她会给出一个立场鲜明的回答,但她却说,已经放下了“死亡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的执念。
以下是我们和上野千鹤子的对话。
一个人的老年生活,乐趣与困惑
三联生活周刊:八岳南麓的土地,实际上你在20多年前就买了,为何2020年左右才决定把那里作为定居地?做出这个决定的契机是什么?
上野千鹤子:当时买那块地,是因为已经有朋友在那里居住。那个朋友那年夏天要出国,于是问我要不要搬去那儿住住看?我在那里生活,在大自然中度过了一段日子,才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这种生活的喜悦,于是买下了那块土地。当时我并没有认真思考是不是就此定居下来这个问题。即使是现在,其实我也还是在两地来回,还没做出决定——毕竟,对年纪大的人来说,城市生活真的很方便。但另一方面,在自然中的生活又是无可替代的。所以,我现在仍然在犹豫中。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在你看来,普通人在选择养老地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或者说,什么样的地方适合度过晚年?
上野千鹤子:20多年前我并没有打算在八岳安度晚年。直到后来开始认真考虑晚年生活的去处时,我才意识到,决定一个地方是否适合养老,比起基础设施条件,更重要的是,那里是否具备完善的医疗、护理与照护资源。
事实上,八岳南麓最初正是一个医疗照护的“空白地带”。但这些年陆续有专业的医疗与照护工作者选择迁居于此,使得原本资源匮乏的地区迅速得到了改善与充实。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我才得以依靠日本的介护保险制度,平稳地照顾并送别了我的一位亲密的老朋友。这段经历让我更加坚定地相信:所谓“自助—互助—公助”的养老模式,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可以在现实中具体实现的愿景。
 日本山梨县富士吉田市的新仓山浅间公园内,樱花盛开,远处可见富士山(视觉中国 供图)
日本山梨县富士吉田市的新仓山浅间公园内,樱花盛开,远处可见富士山(视觉中国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八岳的住所鹿野苑,听说是请了设计师专门按照一个人生活的习惯来设计的。可以介绍一下,这栋为独居生活设计的房子有什么特点吗?
上野千鹤子:是的,设计上有几个特点。整个房子采用了一体式设计(one-box),没有把空间细分成许多小房间,毕竟家里并没有很多人住,所以没有必要。还有一点是,这栋房子做了无障碍设计,因此卫生间也特别加宽了,可以让轮椅顺利进出。此外,卫生间在一楼和二楼各有一个。
说到失败的地方嘛,就是把浴室建在了二楼。这么做的初衷其实不错,因为二楼南侧的视野非常好,从那里能看到很美的景色。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了洗澡,就必须上下楼梯。等年纪大了以后,这恐怕会变得很困难。
三联生活周刊:记得你最初要求卫生间不装门,因为一个人住的时候并不需要,后来还是听从设计师的建议装上了。
上野千鹤子:是这样的,我问过一些独居的朋友,他们大多说自己上厕所时都是不关门的。不过,因为家里还是会有客人来,所以厕所不能没有门——这一点我后来才意识到。有时候有客人来,我也会把门关上。但因为做的不是平时习惯的事,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三联生活周刊:让我比较吃惊的是,你是习惯了都市生活的人,却能够完全适应山中的生活,而且发现许多乐趣。这一点是如何办到的呢?
上野千鹤子:我本来就是个热爱登山和滑雪的人,可以说是典型的“户外派”。所以,待在自然环境中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虽然在乡村生活会有些许不便,但我并不是靠务农为生,也没有打算深度融入当地的传统社区。我更倾向于在自然之中,单纯地去感受和享受自然,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极大的奢侈。在日本的一些地方,其实也存在着“移居者社区”,也就是由和我一样因热爱自然而选择迁居乡村的“新住民”们自发组成的社群。与这些人交往让我感到非常愉快。
三联生活周刊:在八岳的朋友圈中,人际关系的边界感很有趣。老年后建立的友谊,与年轻时的不同吗?
上野千鹤子:朋友是无论到了多大年纪都可以交到的。而且,朋友也有各种类型。年轻的时候,会毫不顾忌地踏进对方的内心,像是赤脚踩进去一样,建立非常紧密的关系。那种人际关系是我们在年轻时会去构建的。可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就会倾向于另一种关系,我们称之为“ゆるとも”,也就是松弛的朋友关系——彼此不过多介入对方生活,但在有需要的时候,却是可以彼此帮忙的关系。
慢慢地,我们会越来越擅长去建立这种类型的朋友关系。比如在感到寂寞的时候,就算不特意把自己内心的痛苦向对方倾诉,只要对方能陪在你身边,一起出去走走,一起吃顿饭,仅仅是这样,也真的能让人觉得得到了救赎。
放下“必须如何”的执念
三联生活周刊:你过去多次论证过一个人终老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孤独终老”还是个难以接受的概念。那么,经过长年思考,你认为独自度过晚年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呢?
上野千鹤子:我平时一直是一个人生活,那么为什么在临终的时候,非得被很多人围着不可呢?我真的无法理解这一点。如果只是一个人生活,身体慢慢衰老,某一天就那样死去了,不是也很好吗?问题只是希望死后能尽早被人发现而已。为此,日本现在设计了介护保险制度。只要年纪到了,就会有叫作“介护经理人”的人来负责管理。这样,去世后大概两三天之内就能被发现。那样不就可以了吗?我也写好了遗嘱,指定了遗嘱执行人。
 在日本长野县,从八岳山脉最高峰上的行者小屋 (Gyoja Goya) 望去,便是著名赤岳的山顶(视觉中国 供图)
在日本长野县,从八岳山脉最高峰上的行者小屋 (Gyoja Goya) 望去,便是著名赤岳的山顶(视觉中国 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说实话,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心态。我发现人很难预测临死前的想法,比如我家的老人去世前,希望挂念的亲人都到病床前来见最后一面,看着那样的场景,我也很受触动。可能不站在生死的临界点上,人是无法知道自己的心情的。
上野千鹤子:人在临终的时候,并不一定能见到所有想见的人。上一辈人大概是那种从出生开始,就从未独自生活过的。而我们这一代人,是在自己的“儿童房”里长大的孩子,中国也是独生子女比较多的国家吧。所以,对于那种习惯了一个人生活的人来说,临死的时候突然被一群人包围,反而是一件很反常的事情。还有一点是,随着社会高龄化的到来,“准备死亡”的时间其实是很长的。如果真的有想在临终前见的人,完全可以趁着有时间提前见面,把想说的话说清楚。没有必要等到最后一刻才匆匆赶来。
独自一人生活这件事,其实不必等同于“孤立”或“孤独”。一个人住,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拥有各种朋友、社会关系,这两件事是可以并存的。所以,一个人生活、一个人死去,并不意味着孤独或者寂寞。完全不需要那样想。如果说我在临终的时候真的有想见的人,那可能不是家人,而是朋友。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八岳送走了自己多年的朋友色川先生。为了帮助色川先生处理身后事,做出了入籍的决定,也引起了一些争论。当时为何做出那样的决定?如果事情发生在现在的话,会有更好的方式解决吗?
上野千鹤子:我败给了日本的法律。日本是一个“家庭主义”很强的国家,而我一直是反对这一点的。比如说,朋友,或者只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即使你陪伴他走到人生的终点,也不能为他提交死亡申报,无法处理他的财产。去银行取钱的时候,工作人员一定会问你:“请问你和这位是什么关系?”如果你说是朋友,那基本上什么手续都办不了。正因为如此,我在照顾色川先生期间遇到了很多麻烦。最后,我也只能无奈地屈服于家族主义的法律,这让我感到非常遗憾。
现在,日本国会正讨论关于“夫妻可选择不同姓氏制度”的提案,这个法律正在提出和讨论阶段,执政党反对这个法案,而在野党是赞成的。我们当然是希望它能够通过的,但目前为止,情况仍不明朗,还不能掉以轻心,真的让人非常为难。在日本,有很多人正因此感到困扰。
三联生活周刊:我在你过去的书中读到,在朋友K子女士的临终护理中,你和朋友们建立了一个30人左右的小团体,你称之为“生命综合管理”。这样一个团体似乎能解决各种护理、法律上的问题。你开始为自己准备一个这样的小团体了吗?
上野千鹤子:在为独身的朋友K子女士送终时,朋友们组成了一个30人的团队。其中有各类专业人士,包括法律、医疗,还有专门从事基金会管理的人。所以,我也在想,如果我将来能有那样的团队就好了。但我不知道,等我需要的时候,是否还会有人愿意为我组建这样的团队。
当时我们组成那个团队的时候,大家都还年轻。可现在大家都已经老了,未来会怎么样,真的无法预料。通过介护保险认定之后,我也会配备一位“介护经理人”。他会从医疗、看护、介护等方面,为我组建一个团队,叫作“照护服务对接会”。但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这个团队不仅包括医疗和介护人员,也能加入法律专业人士、朋友,还有像“成年监护人”(日本法律体系下,为了保护认知能力减退者而指定的成年人监护者)这样的角色,如此就可以建立一个全面支持的体系。
我现在是这么想的,但到了那个阶段是否真能做到,现在还不确定。不过,我已经指定了遗嘱执行人,是一位比我年轻的人。所以如果现在要开始组建那样一个支持团队,交一些比自己年轻的朋友是很重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从30多岁就开始思考老年问题了。你觉得一般来说,我们应当花多长时间为老年做准备?尤其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好准备?
上野千鹤子:这个嘛,其实得等真正到了那个时候才能知道情况怎样。但无论如何,人际关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起来的,所以我觉得花时间去经营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际关系是用钱买不来的。尤其是应该鼓励男性也要努力去建立那种没有利益关系,但能在关键时刻给予支持的人际关系。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另外,通过对老年生活的研究,我也越来越意识到,不断收集信息、拓展知识面是非常重要的。不论面向老年生活,还是面对死亡,信息的丰富程度决定了我们选择的空间与从容的程度。尤其是在现今社会,中小规模、个体性的资讯来源反而可能比宏大的体制性信息更贴近实际、更有用。一直以来,我都在看着比自己年长10岁、20岁的人,他们是走在我前面的人。也就是说,通过观察那些比我年长的人的生活方式,我学会了“原来人是这样变老的啊”。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一个很令我关心的问题是,人在死亡这件事情上到底有多少自主权。如果看护者、家人和本人的意愿真的发生冲突,究竟谁的意志能被贯彻呢?对你来说,到了最后一步,什么事情可以让步,什么事情会坚持?
上野千鹤子:我一直很明确地觉得,自己不想在医院或养老机构终老。但一旦到了无法自主决定的状态,情况会变成什么样,那就是个未知数了。毕竟,人是无法决定自己将以怎样的方式死去的。
我很庆幸自己从事了这项研究。因为我接触了很多人,见证了各种各样的死亡方式。正因为见得多了,慢慢就不再那么执着了。所谓“不执着”,指的是不再固守“死亡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的想法。我不再认为“非得如此不可”。随着对现实理解的深入,人的想法是会改变的。不论老年的过法,还是死亡的方式,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样貌。既然我们无法自己选择将来的结局,我也就慢慢地,把“必须如何”的执念放下了。
 《岁月自珍》剧照
《岁月自珍》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说到底,在八岳生活的老人还是素质很高、经济条件不错的。那些相对贫困的老人,他们的老年生活质量该如何保障呢?
上野千鹤子:非常遗憾的是,当前老年贫困问题十分严重,尤其是女性独居者的贫困状况尤为突出。这与日本养老金制度的设计缺陷密切相关。曾作为雇员工作过的人,还能领取相对体面的养老金;但对于那些自营业者,或者一生未婚、未能持续就业的女性来说,由于长期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她们所能领取的养老金往往非常微薄。因此,要真正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我认为是一项非常艰难的挑战。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我们看到机器人、人工智能技术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养老领域。你觉得科技的进步,能更好地支持人类的晚年生活吗?
上野千鹤子:护理床、护理机器人之类的护理辅助工具,以及各种相关技术的出现,是非常好的事。但是我坚决反对“交流型机器人”的应用,就是那些被设计来替代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机器人。护理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正如孩子必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长大成人。同样,老年人也应该在人与人的关系之间衰老和离世。如果有人认为机器人可以承担这部分工作,那是完全错误的想法。
现在社会上常听说要研发“照顾老人的机器人”,但很少有人谈论开发“照顾婴儿的机器人”。这说明大家默认老人可以交给机器处理,情感层面的需求不再重要。但这其实是在轻视老人,把他们当作“已经衰老到这地步了”“反正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差不多就行”的存在。不管老年痴呆与否,人依然是人,尤其是那些活了几十年、有着丰富人生的人。所以我认为,照顾老人的这项工作,如果能被视为一份真正值得尊敬、有回报的劳动,那就太好了。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第21期。参考资料:上野千鹤子,《我准备好了,变老也没关系》《一个人最后的旅程》《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

排版:秋秋 / 审核:雅婷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5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5978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