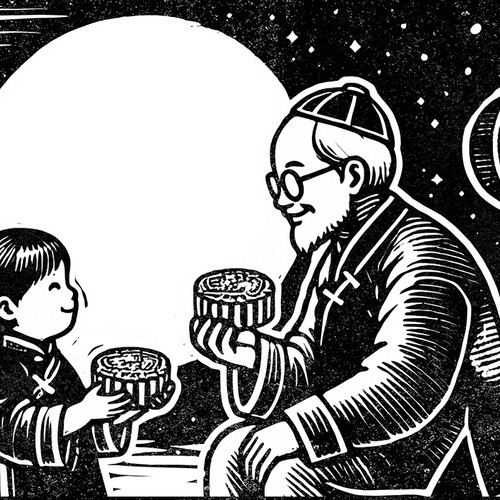有时会觉得父母才是同盟军,群策群力对付各人家里的小祖宗。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我一直与自己的社交恐惧症坦然相处,因为没有什么治愈它的必要。我在实验室工作,同事多半是内向的人,关系不错,所以不必老说话。我的社交圈很稳定,主要是同事。有个笑话说:外向的工程师和内向的工程师区别在哪里?外向的工程师跟别人讲话时,会看着对方的鞋尖而不是自己的。这个笑话也适用于在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凡是要跟陌生人打交道的事情,我都指使配偶去干。他能跟从来不认识的人谈笑风生,如果不明就里,还以为他们是老朋友。
开始送孩子去托儿所以后,我发现日常生活里迅速多了一大批熟面孔,就是同样送孩子去托儿所的家长们。每天固定的时间都会见到那几个固定的人,用自行车载着或者怀里抱着自家的小毛头。我很快就记住了所有小毛头的名字,因为把自己宝宝往托儿所教室一放,他还没开始哭,别的小毛头就会围上几个来叽叽喳喳,我赶快撤退。没有几天,我就认清楚了几位宝宝,他们的父母也就成了“某某妈妈”“某某爸爸”。在“某某妈妈”“某某爸爸”那里,我和配偶也是个“某某妈妈”“某某爸爸”。就这样,家长跟家长互为班主任和学生,通过孩子熟悉了起来。把孩子放下以后,在园外也会笑笑,说两句话。做父母的好不容易摆脱自己家哭哭闹闹的宝宝,常会羡慕别人家已经在那里的孩子乖巧自信,一副托儿所小主人的样子。待有机会,向别的孩子的父母表达这种羡慕,别人却会说:“真的?我送他/她进去的时候可是哭得很厉害呀!”有时会觉得父母才是同盟军,群策群力对付各人家里的小祖宗。孩子稍稍大一点以后,从托儿所接出来他们还不愿意走,要接着跟小朋友玩。父母也不能不凑趣儿,每天去接的时候都要带上一口袋大大小小的玩具,给孩子挣面子和充当一般等价物。最受欢迎的当然是交通工具类,不怕磕碰的铲车卡车推土机,因为它们可以从斜坡上呼啸而下,也可以装满铺花坛的小石子和树皮松塔。其次是各种各样的小车和飞机,颜色越鲜艳越好。我给宝宝带过机器恐龙变形金刚,威力堪比核武器,令他瞬间成为最受羡慕的骄傲小孩。观察小孩的玩具贸易和互动方式,会发现小孩在小孩群中才有真正的自由。小孩之间的互动不讲道理,有的小孩自己在玩,别的小孩过来就推一下敲一下或者把玩的东西推倒,被袭击的那个小孩大多数时候好象没感觉,或者俩孩就笑嘻嘻地开始玩。某个玩具没人玩,只要有一个孩子捡起来玩,别的孩子马上都想玩。有的小孩眼巴巴地盯着要,有的小孩直接上手抢,打起来哭起来咬起来大都在这种时候发生。老师和有经验的家长这种时候都是制止暴力,稍作指点排好等待的基本顺序。有时不用等那个玩具轮到大家都已经又玩别的去了,打架的起因瞬间忘到脑后。太过理想主义的大人按大人心目中的平等和民主秩序安排,反而所有小孩都不高兴,然后大人气急败坏觉得孺子不可教。有经验的家长都知道,小孩的共识就是别人的玩具更好,自己的玩具别人一想要也变得好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自然会发展出各人舒服的相处方式。如果陪玩的父母不是时刻要帮自己孩子撑腰占别人孩子的上风,而是有默契让小孩学习社交消耗精力,大人扎堆儿休息一会,每天放学后陪孩子的时光可以非常轻松愉快。孩子疯跑父母扎堆儿的时候,一些成年人的对话就自然而然发生了。托儿所门外的绿地上,欢乐低幼气氛笼罩四方,社交恐惧症不易被触发。因为送的是大学托儿所,所以父母不是大学的雇员就是学生,最擅长的社交破冰话题就是“你是研究什么的?”谈到这个话题,我才想起“某某妈妈”“某某爸爸”们都有正经工作或学业,不仅是妈妈爸爸。相信别人对我的观感也差不多。配偶是物理系毕业的,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容易遇上物理系出来的人,但是一场托儿所野餐就能遇上两三个出自物理系的爸爸,其中一个的博士论文是研究猛禽飞行的空气动力学。我是学生物的,这个领域的从业者非常多,所以我们的对话旨在找到真正的同行。完全依靠计算机的生物学家与我互为异端,虽然他儿子跟我宝宝有一段时间形影不离;而研究细菌的生物物理学家(他有一对机灵的双胞胎)感叹别的生物都太复杂,我也完全没法共情。
有一个爸爸带着小小的刚会走路不久的小孩,一边看孩子一边看书。配偶瞥了一眼书的封面,是希罗多德的《历史》。配偶有点惊奇,问:“你带孩子的时候还看这个?”那个爸爸不太好意思地回答:“不过是英译本罢了。”后来在一次生日会上,我也遇上了这个爸爸,他又高又胖,头发胡子乱蓬蓬,象一头没脾气的大黑熊。小孩被他小心翼翼地抱在手里,好象抱着一束花。在大学环境之外,带着孩子也等于打了一个“可以随便交谈”的标签,好像有孩子的家庭一定乐于而且善于聊天讲家常。常去的超市旁边有个教堂,有一年夏天办了个儿童游园义卖会,我们周末无事,就去了。去了以后我才发现,组织活动的几位主力成员,连同教堂牧师,平均年龄至少七十五。他们属于这个城市的英国的那一面,而不是学院的那一面。我的日常生活里几乎没有本地老头老太太,所以一开始听他们聊天还挺有新鲜感,不过很快就意识到哪里的老年团体聊天都有类似的特征,重点不在内容,而在加强小团体之间联系,兼打发时间——一个苹果派都能翻来复去说上十分钟,活象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里的背景人物。但是有一个穿大红外套的老太太目光敏锐地注意到了我们一家陌生面孔,主动来打招呼,很快把我们两口子各自从哪里来,在哪里结婚,在哪里工作,什么时候生的小孩全问到了。我一边聊着一边想这怕不就是马普尔小姐的原型,一边觉得红衣老太太居然有一种跟年岁相配的威严,无法回避她那些直截了当的问题。
但她毕竟不是马普尔小姐,而是一个热心本区教堂活动的老太太。当她发现我是一个科学从业人员而且研究的是生物科学以后,她好像在花园里遇上一只浣熊,彼此都不知该怎么办。好在宝宝在充气城堡里发出了欢乐的喊叫,我借机溜走了,长吁一口气。这一次,社交恐惧症竟没有发作。排版:盐巴/ 审核: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