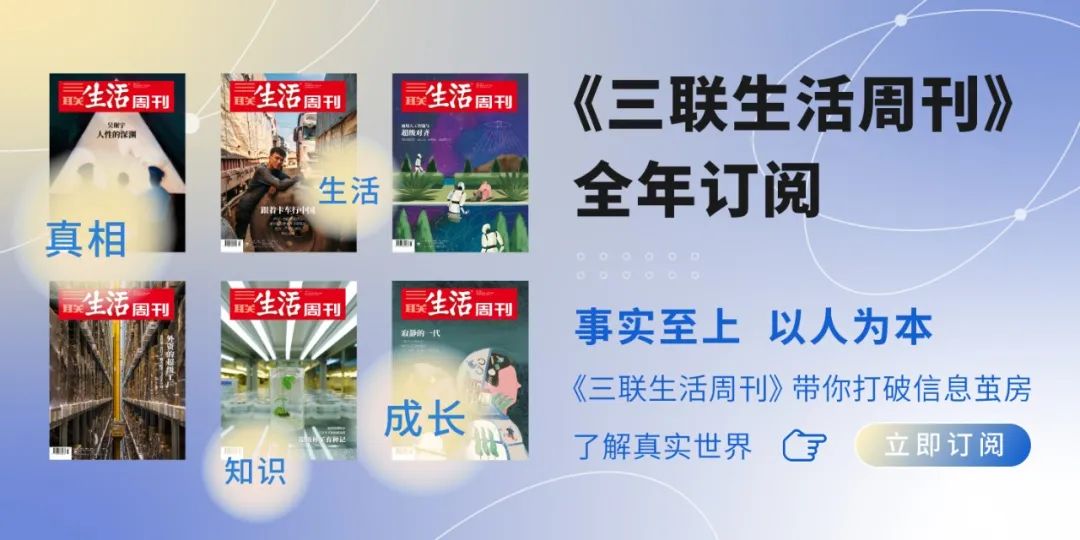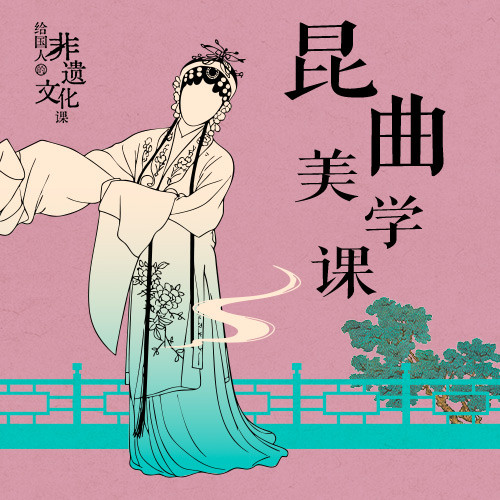当“一辈子都干不成什么”的我,目睹父亲的死亡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10-24·阅读时长25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贾行家
一
一
一
我决定不再等待我父亲的形象到来。
在他离世后的28年里,我没有机会和他对视。我那时在他眼里是个问题,这个问题日益自闭、逆反和肥胖。到我自己也做了父亲,明白这等待是否有希望与时间、经验无关。我不了解他那种近乎庄严的自我意识是从哪里来、是什么体验。他有一颗暴躁而透彻的心灵,怀疑我是不是没有心。
他的信条从三个或有冲突的体系中来:山东东部乡下的宗族;从他幼年开始重整一切也统治一切的新秩序;他是“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生,学的工科;他把这三个系统赋予的身份和使命都完成得很好,哪怕其中有难以弥合的矛盾。

他甚至不需要一个暗处收纳私心杂念。他憎恨我进入青春期后总是关起房门,认为这是阴暗软弱的举动,这是我们父子关系的象征,也是我们的差别之一。
每次活到接近他当时的年龄,我才意识到他比我早熟的地步。对我这种人,还有当年捉弄过他的城里同学,他在学生时代的信中怜悯地说,这些人不是坏人,他们不勇敢,因此一辈子都干不成什么。一个人是什么要看他干了什么。我现在感到恐惧,不知道活过他最后的年纪后该去和谁争论。
他从不怀疑世界的真实性。好像是从一开始就直接按照世界给定他的位置去活,也不怀疑那些像是他选定的而不是接受下来的信条。他的思想方式是一个个算术等式,等号意味着除了已被简明列出的,其余的都不重要。对别人是诱惑的,在他看来是累赘,是对自己的侮辱。
他被任命为副厂长以后,厂里意识到在20多年里没给他分过房子,拨了半栋苏联专家住过的小楼给他,他回绝的理由是家在市里,又不能搬来,用不上这房子,我们家便一直住母亲分配到的两个小房间,那是教育局用半间教室交换来的。除非下班晚了赶不上通勤,他也没用过派给他的小车回市里。他半开玩笑地说,为什么你妈总能评上先进,我什么奖都没得过?可能和他的不合时宜、不在乎其他人的脸面有关。他转而为了我竟然和那些人一样狡诈而悲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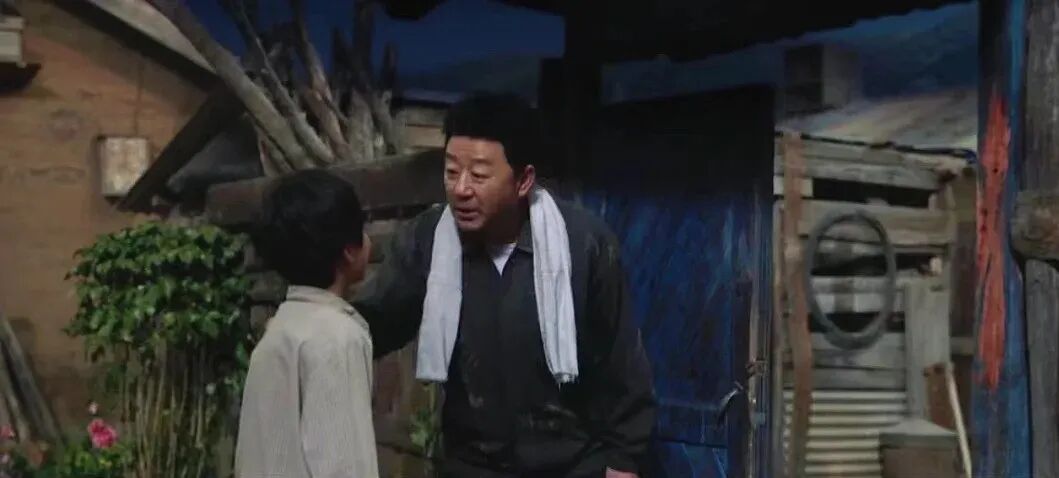
我一直回避和他说话,即便今天,也会反驳他:为什么要那么确定,为什么要认真到这个地步?你在乎的、经过的,终归是虚空。他向来鄙视我长着颗一团乱麻的脑袋,活成了一摊烂泥,这是我俩的另一个差别。
我见过许多比他聪明的人,比他有智慧的不多。我清理他的办公室,读他留下的信件和手稿,检索他的生平,听人回忆,发现品格和言行比他更一致的人,我几乎没见过。这也是他早年立下的守则,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认为我的本质改变不大,我想永远保持这样的本色”。
我多年后得知,他的主要遗产是调到城区后参与的集资建房,他被派过去做“一把手”,原定分给他四楼——没有电梯的七层宿舍楼时代的好楼层,因一个登门向他哀告的下属而换成了二楼,从此我家一直没有光线。那个下属在退休后把那套房子卖了个好价钱。
他的另一笔主要遗产来自死后额外报销的医疗费。他管过万人大厂的经营、采购,在不少南方的关联企业挂名董事长,完全可以从刚出现的时代缝隙里捞出几十、上百倍的数字,换我的话,我一定会。母亲的一个朋友来家向他暗示“别白瞎了这么好的位置啊”。待那人走了,他不解地问母亲:“你怎么会和水平这么低的人来往?”
他清晰的世界观里有一点儿奇怪的混合成分:他应该认可世上的人各有位置,而位置并不均等,他一生的经历都支持这一点;同时,他没有自负或自卑情绪,我从没见过他用不同面孔和方式待人。他不喜欢位置变化引起的关系和态度变化,渴望在日常中摆脱这些。他绝望地反感别人恭敬地称呼他的职务,还有乖觉地故意省略掉“副”的前缀,让他觉得眼前的是个小人——我后来上班时就这样,只要一把手不在跟前,就得省掉那个“副”字,和小不小人没关系,这是这套规矩的气质。他看电视剧里的美国侦探片,感慨为什么不能像剧里那样叫他“头儿”,他不知道自己总是冒犯这个游戏。

厂里都说,那个最年轻的厂长反而最古板。他一直羡慕自己的妻子,只管一个小学,却能容忍庙小妖风大的各色人等,他没法掩饰自己对别人的真实看法。我听母亲和他说过:“要负责,就不能只和自己喜欢的人打交道,人都有特点,只要放对了地方。你说的那人,起码适合去要账。”
每隔20年,他需要处理一次急剧的观念转折,要按刚宣布的新意志完成新的任务。苏联解体时他正在敖德萨,带回了整箱的裤子背带、冰刀和呢子礼帽,忧郁地分给众人,那是那边货架上仅存的东西。
50岁那年,他在北京接受了半年集训,对那里的一切相当满意,生活被重置回大学时代,只有课程、随堂讨论和论文,他喜欢那种规整,也为自己编制了类似的节律。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这里的条件比上大学好太多,又保持着优良传统,宿舍楼的单人房间里有“一张硬板床和蚊帐、一张三屉书桌、一个书架、一个落地台灯、一把椅子、一个立柜、一个脸盆架和放暖瓶的茶几,每个楼里都有阅览室,每层有电视和电话间,6点起床,六个半小时上课,两小时自习,礼堂在晚上会放一部电影”。他看遍了从胡金铨、张彻、王羽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所有武侠片,对导演是谁毫无印象。那大约是他对天堂的想象。
不知道他怎么理解正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我俩说过的话是有数的,他绝不会坐视他人的痛苦,他的心灵比我柔软得多,我能觉察出我的冷漠残忍是出于无知怯懦,那么,他的心软也许是因为更清楚地知道些什么。每个星期天早上,我们兄弟能听到父母在里屋讨论问题,家里的、单位的、社会上的,这是他们多年的习惯,周六晚上入睡前也会聊上很久。
我只记得他捧着那本在上世纪90年代和黄色杂志一道流行起来的《诺查丹玛斯末世大预言》,掐算我们兄弟在1999年世界毁灭时多大,并不知道他自己不会在那一天里。

插图|老牛
二
二
二
多年后,母亲想去厂电视台找一找那些录像,再看看父亲的样子,被我以电视台不会保存为由制止了,何况已经改制了多年。我主要是怕尴尬,怕被认为是依靠父辈建立自恋的可怜人,甚至仅仅因为嫌路远。
我在寒假里去过几次他们工厂。我后来意识到,他那几次是为了带我到厂医院化验,看看我是不是也患有家族遗传的肝病。几年后,他在那里查出来了肝癌。
上个冬天,我挑了个便宜的航班,选了个靠窗座位去看一次那个厂区。当飞机临近铅灰的雪野时,我突然觉得无法呼吸。那边的景象和我想象的差不多,我再度见到了那种层高近四米的红砖宿舍楼,那座成本低廉、占地巨大的厂文化宫,连锁的牌子和店铺里的东西是在城郊和镇子里常见的,而街道的间架布局则很有往昔的气派,时间在这里停滞已久,只有路旁的松树长得极高大——

像我父亲那样的人,也许因为具备某种天赋,或者是因为一直在具体地参与自己的命运,在自身和世界的碰撞里,早早设下了一道道闸门,不被未知的外物冲决。可见的理由是:他生于饥饿和悲伤,自那个起点开始,每一次忠实地朝向秩序和知识去行动,都会因为被拣选,多出一分对自身的掌握,进而获得道路。
行进于这条被自己验证的世界之中,他鄙视虚无主义,看不起私利,他在29岁那年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命运,说正经话,我反对绪(宿)命论⋯⋯这几年,我想问题开阔了一些,有些我吃的苦是我本身的弱点折磨我,我要下决心挖掉那些使我陷入痛苦中的孽根。一个人一生遇到的不顺心的事要远远超过顺利的事。”“世界上凡是比较复杂的事情,大概没有一件是轻而易举可以办到的,每当碰到不顺利的事,我便想凭命运去碰。”
我是那时候最早被宠坏的一批孩子,痴迷于电影《猜火车》和《搏击俱乐部》,依据激素水平重复着几句台词:“我们是被历史遗忘的一代。没有目标,没有地位。没有世界大战,没有经济大萧条。我们的世界大战只是心灵之战,我们的大萧条是日常生活。”“我选择不选择人生,我选择别的一些什么。理由?没什么理由。”这些无价值的理由里有一个根本的理由,我们这些喜欢把它挂在嘴边的孩子不知道这个理由的沉重:最终,一切看上去都会没有任何区别。
人往往到了注定停下时,才察觉到此前的一生都是在失重感中下坠,几乎没有真的掌握过什么,才会想认领刚刚从身上经过的岁月,这是最后时分唯一可能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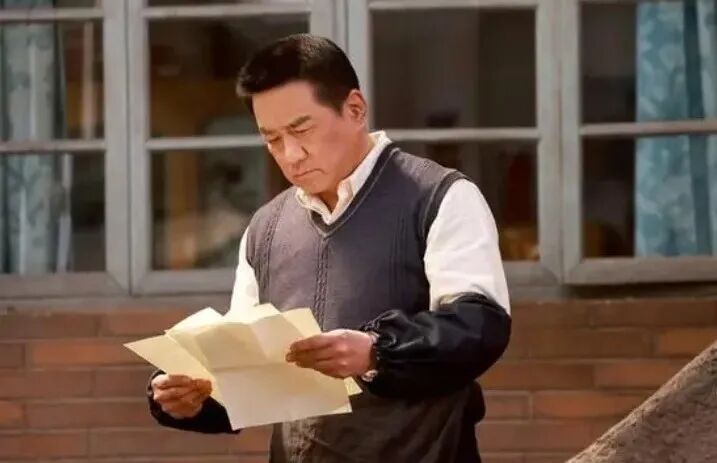
死对他而言是一种打断,那时候,他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着为自己定下的责任,希望凡是他能够照顾到的人都按他意见中的正确方式去生活。我怎么看都不像能考上大学,如果没办法,就把我托付给他的老朋友们,去他们厂读技校,将来念个在职的大专。我悄悄听他俩在小厨房里议论我哥的婚事,我嫂子高中二年级出国前娘家托人来找他们商量婚事。母亲说,他们家级别高,两口子都是大干部,我不愿意巴结。他满不在乎地说是孩子过日子,有什么关系,你不求他,管他高低,非要这么说,我也是司局级,退休以后,这东西有什么用?
他也一直活在对死的预计里,他的母亲、开启了我们家族病史的奶奶,在他13岁那年过世,然后是他的姐姐、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他是被剩到最后的一个。他从面临同样命运的外甥那儿弄清了这病的原理,两个人一直在密切地交流如何吃药和保养,好把各自的事情做完,随即各自失败。他在恋爱时代的信里经常描述这种前景,警告母亲要三思,真正的威胁不只是他们两个人的单位离得太远、他有太多的亲戚要照顾。我听他说过的最泄气的话是:现在看来,我这辈子也做不成多有价值的事,我也没高尚到能把财产都捐出去,也就是干干工作、照顾照顾老人孩子了。
至少在当代,一个人选择了自己在世上的职责,不等于知道该如何自处、知道自己将独自前往何处,与庄重的活相比,死显得太轻易,也太滑稽。
我亲耳听到他在做出决定时说:“多活几年还是少活几年,没什么区别,要看活的质量。现在我有可能手术,就赶紧做,治不好了可以赶紧死,不要成为谁的拖累。”

我知道的另一句话,是父亲告诉母亲这个消息时,先认真地叫了她的全名,然后说“我还是倒霉了”。他说在去澳大利亚考察前,他是特地到厂医院拍了片子的,什么都没发现,或者是设备精度不够,总之回来就有了。已经观察了一阵,去过医大,结果是一样的,现在应该放弃幻想了。
父母告诉我们兄弟的是:他们要去上海旅游一趟。我那年17岁,正常人该能发现这事的不正常,可我只是醉心于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在家,还跑到北京去学了几天吉他。母亲中间回来了一次,把事情向我们说了,在收拾东西回去之前,做了件出离理智的事,让我领她去歌剧院后身的琴行,给我买了一把琴和一架效果器,2800元+2700元,是不小的花费,“既然你喜欢”。现在我只记得那时对这琴的快乐,不记得对他和她有过什么忧虑,我背着那些东西四处赶场,心里只装着自己,这大概就是做母亲的人的目的。她说,你爸在病床上也很后悔,说何必呢,以后不要求你什么了。他希望你上个大学,不是强迫你做什么,是他觉得人经过了几年的大学生活会不一样。
三
三
三
我抱着一大瓶两升装的可乐走在去医院的路上,那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我将近200斤,穿着件父亲当纪念品买回来的白T恤,胸前印着3排9只考拉,其中有一只像抱着可乐瓶子一样抱着桉树。
医院是旧的,前门里面是一座孙中山的坐像,第三天的早上再从这里进来,我意识到他和我刚死去的父亲同岁。绕过门诊,进了住院处的楼,整栋楼里都没什么光,人不多,走廊上有架转运的平车,我那天晚上最困的时候,发现那上边空着,爬上去睡了一会儿,几个小时后,它被用于运送父亲的遗体去楼下的太平间。
我记得他们在病房里面的拐角。床上那人已经不再是我父亲了。蜡做的黧黑面孔有些像他,剩下的几缕头发全都白了,像一片柳絮似的散在枕头上,棉被在随着他的倒气起伏,里头像是空的。床边马扎上面坐着的也不像是我母亲,她从来没有如此恍惚和困惑过,而眼神却亮得异常,近似凶光。
长大和衰老不是线性渐进的,是一节一节的,在某件事上急剧地完成了。当儿童目睹父母陷入绝望时,被迫长大。那几年,很多东北的孩子在以这种方式长大,彻底修正了对世界的看法。和家里下岗的同学不一样,我用另一种方式观看了人的绝境,我在那个晚上同时目睹了他的死,和她强悍的悲哀,多年来,我一直“被那晚的滔滔河水”(博尔赫斯《天赋之夜》)震慑。
母亲一遍遍地叫他的名字:儿子们来了,你看一看,还有什么要嘱咐的?
他说:还不是时候。他把我哥看成我,要我去写作业,说不用管。接着便开始大声呻吟起来。
母亲从病床下掏出藏青色的西装、衬衫、西裤,最后是一件呢子大衣:这是我上午在百货商店买的,寿衣店里的都太难看了,这些都是好牌子的,你看看,咱们穿这些走,好吗?赵姐告诉我把扣子都剪掉。
他说,还不是时候。
父亲从凌晨开始吐血,应该是某个脏器破了,逐渐止不住,无法呼吸。我清楚我父亲真正死去的那个刹那,我一直不错眼珠地盯着他的脸。应该是由于血涌向头部,他最后变回了我父亲,脸色红润,有了表情,在皱眉和抽搐,对灼烧的病痛不耐烦,为了无法清晰专注地想事情而懊恼,然后,就是那个刹那了:有一片来自他体内的光泽,从脸上自下而上地泛起,迅速地如水面上的烟雾一样消散了,也像是关了开关之后灯泡的最后一下抖动。

没有庄严的退场,只是消失。“别再看我,你看到我死了我会羞愧的。”(普拉东诺夫《切文古尔》)我时常想起这句苏联小说里的对话。他也是那样的人,对他而言,我这种弱者不懂:活的意义,早已先于个体被设置在生活和群体之内了,那些意义是如此清晰可见,人越是行动,越会感到意义的真实,否则,生活就不值得一过。他临终前叹息“还不是时候”,是为了那些不得已卸下的重负而不甘。还真是,我向来怕责任,认为那是对“我”的打断,我觉得世间的责任只有被装扮出来的意义。而他如此投入,如此厌恶在将职责推向目标的路上被死亡所打断,他尝试依靠理性去和命运商讨能多行动几年。
父亲也许是最后一代那么活的人了,在几种坚硬的秩序之间,找到了把它们全担下来的方式,他也因此拥有了一个意义丛生的位置。
更晚些时候,病房的事料理完了,盖上了单子的死者被送走。帮穿衣服的是父亲单位的同事,姓丁,很快被提拔成了办公室主任。丁主任又带我们到水房去擦洗,嘱咐我脱下胸前染了血的卡通考拉T恤,不知从哪儿拿出件换洗衣服,说沾血了,不能留。我有点儿可惜,想坚持一下,那血衣是父亲买给我的仅有的一件衣服。丁叔看了我一眼,今天的我回忆,他那时是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想用眼神提醒我:你不配承受,因为你不能理解。

那一年我大概四五岁,在我们最早的那个半间教室改成的家里,父亲凌晨刚下火车,把我从床上摇醒,迫不及待地展示他在大连出差时买到的铁皮海豹顶球玩具,蓝色的海豹在地上转着圆圈,翅膀一下下地上下忽闪着,我刚从一个梦中醒来,也蛮喜欢现在的这个梦。海豹头顶的那个球和发条钥匙很快就被我丢了,海豹因为被泡在水盆里玩,再也不动了,我把它撬开,只得到一个生锈的“发动机”,摆弄了两天,想不出什么玩法,也扔掉了,那只玩具是这样一点点消失的,关于我父亲的印记也大概如此。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39期封面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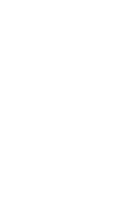
排版:球球 / 审核:小风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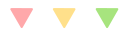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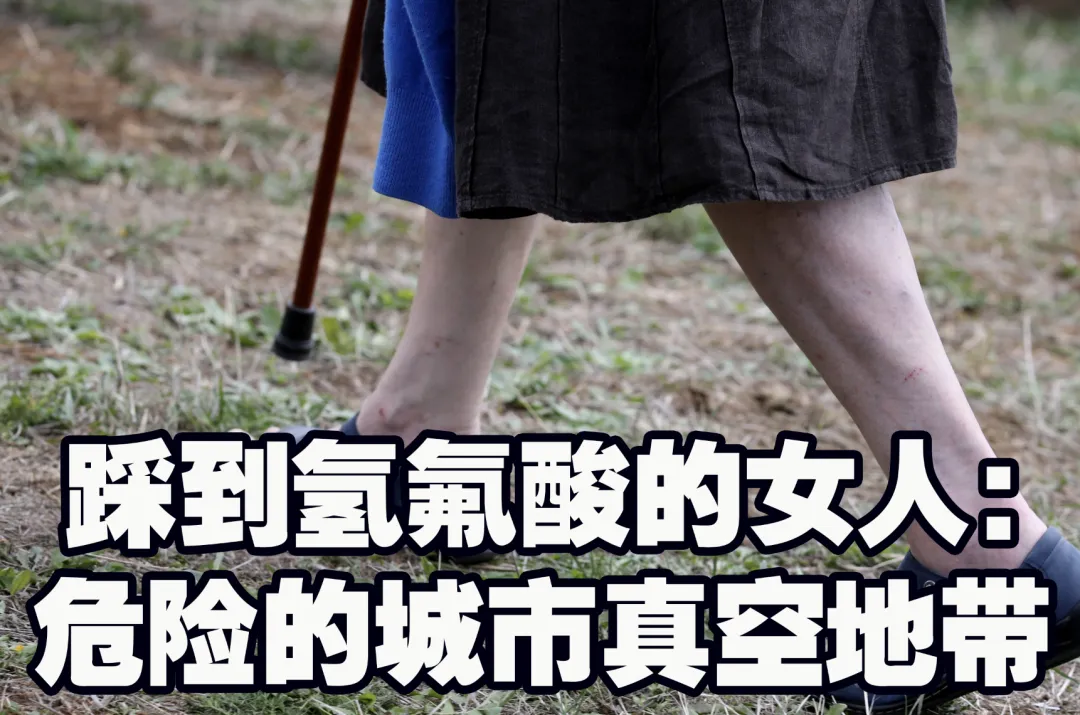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1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6162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