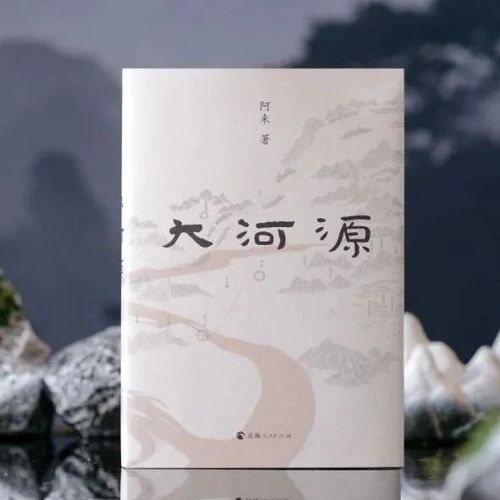以天下为己任:宋代士人的登峰与造极
作者:贾冬婷
2018-01-26·阅读时长22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11178个字,产生550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士风”萌出
若论宋代士大夫“先觉”精神的首倡者,当推范仲淹。他在《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成为当时乃至后世士人的座右铭。南宋思想家朱熹在《语类》中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且不论范仲淹是否完美践行了“以天下为己任”或“先忧后乐”,但在他提出这一新规范之后,很快便在士大夫群体中激起了巨大的回响,以至于朱熹评价他“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
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以天下为己任”不仅是朱熹对于范仲淹的论断,事实上也可以看作宋代士大夫对自身社会功能的一种规范性定义。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普遍意识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余英时认为,“以天下为己任”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通向宋代士大夫内心世界的大门。
余英时在其著作《士与中国文化》中提出了中国“士”的传统。如果从孔子算起,这一传统至少已延续了2600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相对应的,中国的“士”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余英时认为,以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而言,儒教始终居于主体地位,佛、道两教在“济世”方面则退处其次,这也是传统中国的“社会良心”为什么必然要落在“士”阶层身上的背景。
“士”的社会角色由孔子最先提出——“士志于道”,规定“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弟子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对后世的士人群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士”的传统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但这一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中国历史上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余英时概括,“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而在秦汉以来的2000年中,每一时代的“士大夫”又与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相呼应。秦汉时代,“士”的活动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以儒教为中心的“吏”与“师”两个方面。魏晋南北朝时代儒教衰落,“教化”的大任从儒家转入释氏的手中,“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道家名士以及心存“济俗”的佛教高僧反而更能体现“士”的精神。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徒继续其拯救众生的悲愿外,诗人、文士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心”。及至宋代,儒家复兴,“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新风范不仅是原始儒教的复苏,而且也涵摄了佛教的积极精神。北宋云门宗的一位禅师说:“一切圣贤,出生入死,成就无边众生行。愿不满,不名满足。”一直到近代的梁启超,在他“世界有穷愿无尽”的诗句中还能感到这一精神的跃动。
余英时认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直到宋代才完全明朗化了。先秦的“士”主要是以“仁”为“己任”,他们是价值世界的承担者,“天下”则不在他们肩上。东汉是历史上一个士人群体闪耀的时代,当时士大夫领袖李膺提出“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仍然局限在精神领域之内。而宋代范仲淹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风范,“以天下为己任”一语才开始传播,激发了一代士人的理想和豪情。如果用现代观念作类比,可以说“以天下为己任”蕴含着士人对于国家和社会事务有直接参与的资格,成为“士”的集体意识,并不只是少数理想极为高远的士大夫所独有。
那么,为什么一种“士风”——士人群体特殊的精神风貌会特别显著地出现在宋朝呢?或者说,宋朝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士的黄金时代”?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告诉我,并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宋代就是“士的黄金时代”,当时并不是没有针对士大夫的狱案或整肃,比如乌台诗案、元祐党籍、庆元党禁,但宋代政治文化环境相对宽松,确实是学界共识。这种较为开阔的政治空间为士大夫力量的形成、为其参政议政及学术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适宜的外在条件,因此士人群体思想活跃,精英辈出,呈现一种水涨船高的整体氛围,用欧阳修的话说,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于上乘。”
邓小南认为,这一变迁的发端不是宋代,而是在唐朝中期就出现了。“唐宋变革”论是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在上个世纪初最早提出的,他甚至说“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从唐代后期到宋代早期,北方士族靠着谱牒的政治优势而形成的“旧世界”,在延续了几百年后最终在社会动荡和时代变迁中消失了。旧的士族随之衰亡,一个新的士大夫阶层取而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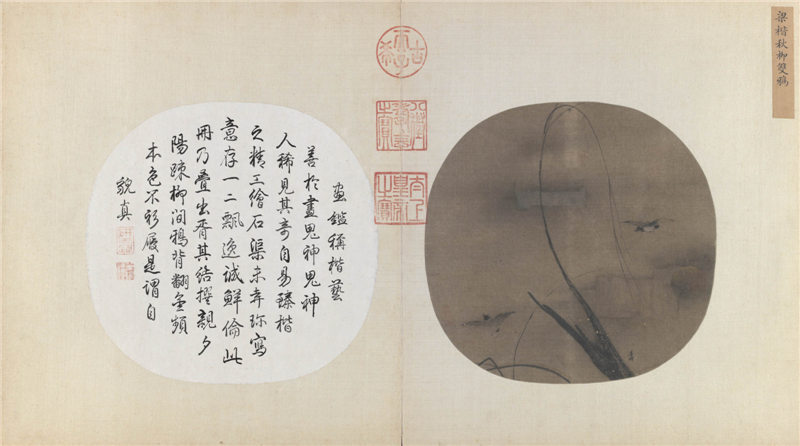
文章作者


贾冬婷
发表文章79篇 获得77个推荐 粉丝1345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助理、三联人文城市奖总策划。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