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世界的方式应该是多元的
作者:肖楚舟
11-26·阅读时长17分钟

刚刚从热带国家回到韩国的金草叶,在首尔的卫星城高阳市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坐在咖啡馆户外的座位,金黄的树叶铺了一地。我们在经历冬天前最后一股异常的暖流,气温接近20摄氏度。
从生化专业硕士毕业后,金草叶下决心“当一年全职作家试试看”,没想到出道就成功,就这样过上了自由的创作生活。高阳是金草叶的工作室所在地,但不是长居地。这里曾经是首尔的“睡城”,无法负担首都生活成本的上班族们,在这里度过一个个夜晚。城市的重心不断转换,现在,这里的街道上多是老人和孩子。工作日的中午,满街散发着咖啡和烘焙的香气。
在韩国科幻文学圈中,“90后”作家金草叶被视为改变风向的关键人物。2017年,她的小说《馆内遗失》和《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在第2届韩国科幻文学奖中同时获得两项大奖。《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是金草叶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2019年至今,累计销量超过35万册。在此之前,科幻文学在韩国并未进入主流文学视野,直到21世纪初,在韩国年销量超过3000册的科幻小说还屈指可数。照她自己的说法,“起初想着能卖出一万本就不错了,结果很快加印,最后半年内卖出了3万册。现在想想,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到底是为什么呢?”
如果从读者的评论里找答案,原因可能是“温暖”“细腻”“充满爱”“科学与抒情的结合”,但这些抽象的形容词都难以传达金草叶的故事给予人的复杂感受。那是一种真诚面对现实,又轻巧地脱身而出的过程式体验。
最初打动我的故事是《馆内遗失》。在存储逝者思维的数字图书馆,智敏妈妈的“思维”不见了。明明在活着的时候几乎哪里也不去、怎么也不可能失踪的妈妈,却在死后走失了。为了找到图书馆里存储的“妈妈”,智敏去找妈妈的人生索引。
在讨论数字思维技术的段落之间,现实的刺痛感在不经意的地方冒出来。智敏想找妈妈的原因是她怀孕了,周围人似乎问候、关心的都不再是她,而是腹中的胎儿。而她却感觉不到对胎儿的爱。为什么会这样?她该把自己放在哪里呢?
很多句子说的是过去的妈妈,也像是在说未来的智敏。妈妈怀孕后辞去了工作,患了产后抑郁,后来和女儿的关系也不算融洽。除了智敏,和妈妈相关的人只剩下七年前断绝关系的父亲和偶尔打个电话的弟弟,妈妈好像没有自己的身份、特征、性格。图书馆管理员提议可以试试用能唤起逝者记忆的物品来帮助检索,列举了一系列过去成功的物品,如亲手制作的手工品、饱含感情的书信,“还说,如果逝者曾经是上班族,工作成果也可以作为输入信号尝试一下”。可惜在智敏的印象里,妈妈不是。“人生与世界失联之后,依然是人生吗?”
女性自我迷失的话题已不新鲜,思维存储也是常见的科幻设定,说起来并无新意的事实,因为被笼罩在“遗失人生”的主题下而震耳欲聋。爸爸那里真的存有一些妈妈的东西,但是很难称之为“妈妈的遗物”,它们都是关于别人的——关于孩子的育儿笔记,孩子的玩具、衣服、相册。在活着的时间内,妈妈早就遗失了自己。最后唤回妈妈的是几本纸质书,妈妈曾经是出版社的设计师,那些书的封面是妈妈在生下智敏前设计的。在故事的最后一部分,妈妈以自己的名字登场,“银河的眼角湿润了。她伸出手,握住了智敏的指尖”。
不熟悉科幻作品的人,哪怕不将金草叶的故事当作科幻来读也没有关系。它有种令人安心的熟悉感,大多数时候,你以为那只是一本都市小说的开头。《情绪实体》是这样开场的:“预定为特辑报道写一篇影评的评论家两次推迟交稿期限……摄影师又因为版权问题突然来找碴儿……新入职的编辑找不到能够代替那篇影评的稿件,最终打算亲自撰写。”《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里面,奉命去废旧太空站驱赶不肯离开的“钉子户”老太太的,是一个“外派人员”,原因是人造卫星太多,管理公司便委托中介处理。选拔能够首批穿越太空隧道的人类时,48岁的姨妈在景获选,却因为她年纪大、没有特别的履历、体形瘦弱还生过一次孩子而引发争议。在那样遥远的未来,不公依然理所当然地存在。
在见到金草叶之前,我先见到了她的中文译者春喜。春喜在韩国读文学博士,平时经常到图书网站查看新书,如果有感兴趣的新书就会试着翻译看看。她读到的第一篇是《朝圣者们为什么不再回来》,这个故事立刻触发了她的兴趣。尽管当时“金草叶”这个名字在国内还无人知晓,她很快翻译了样章,向出版社推荐。
《朝圣者们为什么不再回来》以常见的乌托邦式叙事开头,接下来不断在嵌套的结构内反转。在某个遥远的“村庄”,孩子们成年时便会去“发源地”远行,最后有人回来,有人不再回来,那些人很快就被彻底遗忘。村庄的孩子奥莉芙为了揭开“朝圣”的真相,前往“发源地”地球,在那里,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脸上的疤痕是丑陋的,是会招来恶意与践踏的。原来,她们所在的村庄是由奥莉芙的母亲、地球科学家莉莉一手创建,莉莉因为无法接受自己的先天缺陷而研究出了完美的基因技术,这项技术却引来对缺陷人群的歧视与仇恨,进而制造出基于生理差异的隔离制度。
到此为止,这还只是一个关于技术双面性的普通科学寓言。第一重反转发生在莉莉怀孕后,她发现女儿也和自己一样有遗传疾病时,没有选择废弃这颗胚胎,而是写下了一句话:我在由此证明自己没有诞生价值吗?她为女儿留下了一个遥远的乌托邦,也给村庄的人们留下自主选择的机会:你可以去看一看地球,自行决定去留。第二重反转关于奥莉芙,她没有回到村庄,而是返回地球与自己同样有身体缺陷,同样在歧视中反抗的爱人生活在一起,因为“爱是与那个人一起对抗世界”。

吸引春喜的是韩国新一代女性的勇猛。如果和《82年生的金智英》相比,过去的作品主要讲述的是传统家庭中的女性困境,而金草叶这一代年轻作家,提供的是一种解决方法和可能性,“并非被动地受苦,而要反抗。女性可以通过科技将自己变得更加强悍,从而对抗这些问题。她一方面消解了完全的现实主义的苦涩感,另一方面提供了解决现实困境的途径,这一点大概是她受到年轻读者喜欢的原因”。在春喜所在大学的国文系,过去学界对类型文学的轻视正在改变。“在金草叶出道以后,我所在的院系,包括写作专业的本科和硕士课程,都会专门讲解幻想文学和科幻文学的写法。曾经撰写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家,也会尝试这种写作方式。”
解构中心的叙事法,站在边缘向中心眺望的视角,让金草叶的故事产生辽远开阔的质感。因为先天缺陷被孤立的边缘人群,因为航天技术更迭而永远无法和家人团聚的科学家,被遗落在虫洞另一头的老旧机器人,总会找到自己存在的方式。哪怕时间、空间、物种或者技术成为沟通的障碍,也总能用嗅觉、视觉、触觉,用心找到听懂彼此的方法。金草叶在后记里写:“总有一天,人类会以不同于现在的面貌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但是在那个遥远的未来,也会有人感到孤独,渴望接触。不论生活在哪里、哪个时代,我都不想放弃彼此理解。”
更广泛的视野内,以女性作家和读者为主体的韩国科幻浪潮,展现出一种新的呼唤。梨花女子大学教授延南京(Yeon, Namkyung)将以金草叶、金宝英、千先兰、郑宝拉等作家为代表的韩国科幻浪潮放在一起讨论,她认为阅读科幻小说是女性更有效地回应性别困境的手段。她们联结的不只是女性,还有一切被主流社会视为“他者”的群体。“这股热潮由20~30岁的年轻女性读者主导,通过与女性主义运动的联动形成了韩国的‘科幻现象’。女性读者逐渐掌握了科幻这一工具,科幻既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也是超越传统文学框架的思辨实验,通过探索超越个体主义和性别规范的路径,创造一个相互连接的未来。”
金草叶的成功之所以可以称为现象级,是因为她的写作真正改变了韩国读者的阅读口味,让主流文学的读者将目光投向了科幻文学。延南京为我提供了一组数据,根据2020年韩国教保文库的统计,从1月到9月20日,韩国小说的销售额比前一年增长了30.1%,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其中科幻类作品增长了约5.5倍。在线书店“阿拉丁”发布的统计显示,科幻小说读者中20岁女性的比例从1.4%(1999~2009年)增至12.6%(2010~2019年)。从《82年生的金智英》到金草叶,读者的选择背后,延南京看到的是对另一种现实的渴望,对连接感的呼唤,“从‘解放的读者’到‘反抗的读者’,此次手捧科幻文学的读者是与社会性他者‘连接的读者’”。
当我们离开咖啡馆时,发生了颇有戏剧性的一幕。咖啡馆里一位女士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站起来,“请问您是作家金草叶吗?我和丈夫都是您的粉丝”。她请金草叶在一张白色卡片上签名,那原来是她的婚礼请柬。桌旁,几位朋友都在为她感到高兴,轻声欢呼起来。

现实感是让人“心动”的要素
源于生物学的兴趣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故事常常与现实呈现有趣的关联性。比如《馆内遗失》,本来这个词是用来形容在图书馆内丢失书籍的情况,你却用在人身上,写了一个在人海中失去自己身份的母亲。能否讲讲,你是如何将现实生活中的普通瞬间移植到未来世界的?
金草叶:我的创作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从科学素材出发,研究如何将科学和我们的情感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从而充分展示科学本身的特征。另一类就是从情感出发的,比如我脑中会浮现出一个孤独的老太太坐在太空站里,背对着我们的画面,这样的画面出现之后,我会反过来思考,如何让它变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我需要哪些科学素材来构建这个故事。比如,脑中出现了一个女人跳进大海,却不是为了自杀,而是想要游泳这样的画面,这是我想象中一个日常的场景,但是并不完全符合现实生活,对吧?我的灵感常常来源于这样的画面,它感觉像日常生活,但又有些不同寻常。
三联生活周刊:我读你的作品,非常喜欢那些关于日常生活的描写。比如《情绪实体》里的上班族生活、都市青年的恋爱日常。即使是《息影》这样离我们很远的故事,里面最动人的气味仍然是“袜子在沙漠里被发现时戴着帽子”。为什么在高度虚拟的故事中,现实的质感依然重要?
金草叶:我对小说的评价标准是比较传统的,那就是能不能让我“心动”。如果没有能触动我情感的点,我就会把素材放一放。当我的心被触动,可能不是悲伤或者喜悦,而是某种对未知的怀想,或者突然想去冒险,我就会把它变成故事。如果太不现实,我在读的时候无法产生共鸣,也无法心动。即使我想写不现实的故事,我也会在里面加入现实的元素,感觉和此时此地有联系,心才会被触动。当然,我也在寻找平衡点,在自己想写的远方的故事,和能与生活在此刻的人们产生共鸣的故事之间来回穿梭。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故事里,处于边缘的人物非常重要。比如被科技发展抛下的人,被遗落在另一个星球的人,为什么对这样的群体感兴趣?
金草叶:从接触科学开始,我就对科学的两面性非常感兴趣。我本来以科学为信仰,但逐渐意识到,当科学影响世界、影响人类的时候,如果不加以反思,仅仅追求结果,那是多么危险。大学的时候,我接触了科学哲学的课程,从社会建构的视角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这些内容也体现在我的作品中。创作本身就是讲述变化的,停留在中心位置的人,如果故步自封,那么真的很无趣,这是创作技巧层面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说到科学的两面性,当下最让你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金草叶:目前我最担忧的是人工智能的单一化发展。科学总是与资本相关,没有资本投入技术就无法发展。现在几乎所有资本都集中在人工智能技术上,但资本的本性并不是关心人类,而是为了自身扩张不断向前。那么集中在这方面的资本真的能造福人类吗?我觉得可能不一定。不过这其中也有复杂性,我自己和身边的朋友也在借助人工智能进行资料查询,确实很有帮助,目前来看这项技术是有用的,但未来是否依然如此呢?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吗?人类该如何应对呢?我想我们正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环境中生存。
三联生活周刊:有没有把这样的担忧融入到作品中呢?
金草叶:在韩国,女性的身体经常被利用,技术确实会放大这种风险,它似乎是一种能够将小规模威胁变成大规模危险的工具。这与枪支问题有点类似。如果没有人拥有枪支,大家就不会相互威胁,但一旦有人拥有,你就也会需要枪来自我保护。技术也是如此,一旦一些人掌握了,其他人也不得不使用它来保护自己,并不是为了攻击,而是为了自卫。这就是为何我认为女性和社会弱势群体更应该了解技术的原因。与其远离技术并将其视为负面的东西,不如将其转化为我们的武器。这种态度是当前阶段需要的,但这并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我的感受也非常复杂,最近也在围绕这个问题进行创作思考。
三联生活周刊:你经常在小说中发明非语言的交流方式。比如用色彩沟通的外星人,用鼻子读取空气粒子的新人类。这源于某种对现代人交流状况的焦虑吗?
金草叶:这还得回到我最根本的兴趣上。我从小就对大脑非常感兴趣,好奇人类的意识和自我到底如何形成。我并不在意别人说了什么,而是想知道这些话是如何在大脑中生成的。如今生物学的研究范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人们认为“心灵”存在于大脑之中,但现在的观点是,整个人体都与人的意识相关,这反映了神经科学的变化。我自己的观点也经历了这样的改变,从思考“自我如何被构建”转向思考“我如何感知并通过大脑产生‘这部分属于自我’的感觉”,这让我更加关注人类的感官。当我们在交流和沟通时,往往只聚焦于某一种感官,我希望能够突破这一点,这种兴趣引导我去探索新的沟通方式。读者们往往倾向于从社会视角解读我的作品,而对我来说,这更多是源于生物学的兴趣。
三联生活周刊:这让我想到你的《玛丽之舞》和《萝拉》,两篇都是在谈论人的身体一部分被机器取代以后的情况。“赛博格”这样的话题已经成为科幻文学的主流,当我们的意识和身体不一定同步,我们怎样去定义人的存在?
金草叶:赛博格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许多人把赛博格视为美学上的消费品,但那无法展现赛博格的本质。人类和机器并不总是那么契合,即使改造身体,问题往往隐藏在意识内部,而非外部。当我用机器改造身体,它真的还能算我身体的一部分吗?还是只是外在的补充?某种程度上,我们将所有记忆都交付给智能手机这个行为,就可以看作人类正在外包自己的大脑。正因为如此,我才想记录这些现象,因此开展了创作。
离开的人,留下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故事里经常出现离开的女性。而且她们不是因为生活挫败而被迫离开,反而是在人生顶点进行的主动选择。比如明明被选为宇航员,接受了身体改造的在景,出发前没有坐上飞船,而是跳进了大海。为何塑造这些具有“离开的勇气”的女性?
金草叶:在当下的韩国,年轻女性流行着这样的想法:必须离开韩国。这种相互怂恿的氛围一度很流行。我对这种心态并非完全无法理解,但这促使我更加深刻地思考“离开”的意义,因为“能够离开”其实是有条件的,只有满足某些条件的人才能选择离开。即使知道身处的世界正在崩塌,知道只有毁灭等着自己,也有许多人无法选择离开。因此,我不认为离开一定是解决问题的答案。我的故事中通常会设置两种人,离开的人,和选择留下的人,这反映了我既认可离开,也认可留下的态度。离开本身象征着改变,改变总比停滞要好。相比一成不变,还是变化更有价值。所以作为一种“变化”的象征,我经常在作品中选择“离开”这个主题。
三联生活周刊:年轻女性产生了要离开韩国的想法,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金草叶:大约在2015年左右,韩国的女性主义经历了一次“重启”。尽管许多女性试图改变韩国社会,但仍然感到极大的绝望。她们认为无论如何努力,韩国也不会改变,与其如此不如离开。我不觉得这种选择完全错误,因为它让女性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即使有人离开,也一定有一部分人会回来。一旦视野被拓展,就很难再回到过去的状态。不过,这让我也开始关注那些无法离开的女性。离开的人可能是找到了海外的工作,或者通过努力学习进入国外的学术或研究领域。但这实际上只对一部分有特定能力的人开放。所以,我对这种现象有复杂的感受。
三联生活周刊:之前你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到,中国读者会比韩国读者更在意你的“女性作家”身份。你的故事几乎全部是以女性为主角的,这是无意的巧合,还是有意的设计?
金草叶:在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故事媒介中,男性为主角是常规,只有在必须是女性角色的时候才会设置女性。我的做法就是很简单的倒置,女性是主要角色,只有需要男性的情况下才设置男性。但我发现,很多时候没必要设定男性角色。而且因为读者看过太多男性角色,各式各样的男性角色都有刻板印象,所以反而用女性角色来创作能突破很多既定印象,故事反而更有趣。作为创作者,这对我是一个愉快的挑战。

三联生活周刊:无法离开的人,很像扎根在原地的植物。你在长篇小说《地球尽头的温室》里构建了一个女性的末日乌托邦,而这个乌托邦的核心还与植物有关。你在后记里提到父亲说的一句话,“植物无所不能”。怎么会想到构思这样一个跟植物有关的乌托邦?你怎么理解父亲的这句话?
金草叶:在写这部作品之前,我和父亲去过一家以温室为主题的咖啡厅,当时我脑中就浮现了一个想法,要写一个跟温室有关、植物为主角的故事。正巧,我爸爸学习的是园艺专业和植物学,所以我就不停地问他很多基础的问题,比如树和灌木的区别是什么?花的分类是怎样的?植物学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后来因为我不停问爸爸,这样的植物可能存在吗、这样的事情植物能办到吗,爸爸就说:“植物无所不能,世界上有很多奇怪的植物,你怎么写都行,这些植物都是可能存在的。”
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的想法开始产生变化。我曾经把植物视作一种静态、被动的存在,但它们和女性之间的关系让我有了新的联想。我意识到,地球上最强大的植物也可能是攻击性很强的,有机动能力的,而它们可能是地球上最后存活的生命。现代女性也可以是坚强的,有攻击性的,这一点已经成为常识。另一方面,我也发现那些看似安静被动的女性,她们的坚韧品质值得肯定,我希望能在不否定这一点的前提下,依然表达女性的强大。
从过去到未来的执笔者
三联生活周刊:很有趣的一点是,你关于女性和植物的联想,让我想起作家韩江的《素食者》。你们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作家,却同时把女性和植物联系了起来。
金草叶:事实上,我发现女性和植物之间一直有相似的历史。从很久以前开始,两者都一直在被忽视和贬低。植物学这个学科常常被低估,许多植物学家都在呼吁植物在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植物学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女性也在为自己争取存在的空间,过去女性常常用草药进行治疗,却被称为“女巫”。现在,传统的草药治疗被科学替代了。而科学往往被认为是男性主导的领域,可以说,“科学有一张男性的面孔”。
三联生活周刊:怎么理解这句话?
金草叶:我从小就很喜欢科学,科学给了我很多安慰。但尽管如此,我认为科学那种单方面的、居高临下的分析,背后总是存在着某种暴力性。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最需要警惕的就是这一点。另一方面,正因为有这种俯视的视角,我们可能错过了世界的许多部分,无法真正理解事物的全貌。最近生物学上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就是,许多事物是无法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分析的,传统的方法在扩展人类认知这方面显然有局限。从某种角度看,这似乎与固有印象里的一些“男性特质”相似。
我们需要整体性的视角,当我们放弃那种“全知全能”的想法,新的方法就产生了。哪怕仅仅观察某种事物的形成过程,即使无法获知全貌,也能与其共存,从而形成某种“连接主义”。最近人工智能正向“连接主义”转变,这也让该领域的技术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我想我们分析世界的方式也应该是多元化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作品在韩国引起轰动,可以说是带动科幻文学的热潮,也在国外广受欢迎。现在回头看,你觉得为何能产生这么大的反响?
金草叶:可能是因为我的小说让人心动,所以读者喜欢吧?当我读到一个故事的时候,感受到心灵深处某个地方被触动、留下回响,我就会喜欢上它。如果一味模仿传统文学的风格,我反而会觉得困难。过去,我这样的小说可能会被认为过于通俗,曾经的文坛认为好的作品应该让读者“困惑”,而不是首先感动。我偏离了这种共识,可能因此获得了大众的共鸣。
三联生活周刊:韩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非常强,为什么最近几年读者转向了科幻文学呢?
金草叶:近年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意识到,科幻文学是当下非常需要的。典型的例子是疫情和气候危机。过去的文学大多数只关注人类的故事,非人类只是作为点缀出现,甚至根本不存在,但疫情和气候危机都不是单纯的人类问题。在科幻文学中,人类与非人类是平等存在的,我认为,这正是最适合反映这个时代的文学形式。虽然读者们更可能是被故事的趣味性吸引,但实际上背后的原因是,科幻文学最能准确地描绘我们所处的世界。
三联生活周刊:近几年中国读者了解到的韩国作家,其实属于不同的世代。比如“60后”的孔枝泳、“70后”的赵南柱,你属于年轻的90后一代,你认为不同年代的女性作家,关注的焦点会有什么不同?和前辈相比,你们这一代人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
金草叶:我认为韩国社会真的是剧变的社会,出生年份相差五年,人们的经历就会截然不同。一代代女性的理念变化很快,社会现实的变化却很慢。比如七八十年代的女作家们写的更多是与父权制的斗争,现在,同龄人结婚的不多,逐渐开始摆脱父权制,但仍然有无法摆脱的部分。不同年代的女性作家生活方式虽然不同,却都在捍卫女性的权利。所以尽管经历不同,本质上是相同的斗争。比起差异,我更关心女性作家之间的共同点。
文章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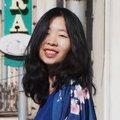

肖楚舟
发表文章0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110人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






